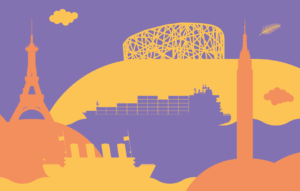棕榈油产业始终充满了争议。它是东南亚的骄傲,在当地创造了可观的就业机会,并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棕榈油被誉为是一种可持续的、用途广泛的油类。与其他低产油料作物相比,油棕因其高效的土地利用率而备受赞誉。
然而,棕榈油行业所引发的问题也比比皆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为开拓种植园而清除泥炭地森林的行为。在媒体报道中,相比于失去栖息地的惹人怜爱的动物,许多靠在森林里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东南亚土著群体却并未受到同等的关注,比如马来西亚的嘉海族(Jahai)、菲律宾的阿埃塔族(Agta)、泰国的马尼族(Maniq)和苏门答腊的奥兰林巴族(Orang Rimba)等。
正是因为有了“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这样的组织所开展的全球认证计划,让全球各地的人们相信棕榈油是一个好的产业。英国著名的“纪录片之父”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甚至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播出的系列节目《七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鼓励消费者购买经可持续认证的棕榈油。但是,“可持续”理念本身就蕴含了政治。为了谁而可持续?可持续的目的又是什么?

RSPO认证计划的审核人员可能忽视了那些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们。这些人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并且往往过着游牧的生活,所以他们所担心的问题并未得到关注。在棕榈油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征询土著居民的意见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在苏门答腊,一家种植公司绕过奥兰林巴族,直接从州政府那里获得了土地使用授权。因此,可持续性认证计划最终可能只是促使企业走过场式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忽视土著居民对可持续性的实际追求。
此外,对于那些已经受雇于种植园,居住在种植园附近,或已经被种植园非法抢占土地的狩猎采集者来说,种植园是否符合RSPO标准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相当于一种“漂绿”行为。对于英国消费者而言,棕榈油上的“可持续”标签可能掩盖了它们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并不可持续的事实。
油棕种植的殖民地根源
当代棕榈油种植园对狩猎采集者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殖民主义。尽管油棕(Elaeis guineensis)原产于西非,但英国、法国和荷兰为了牟利将其进口到了东南亚,而种植园的扩张靠的是土地掠夺制度。
这些殖民主义者通常依靠劳工和剥削土著工人和移民工人来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20世纪初英国人威廉·利华(William Lever)尝试采用这种“工人-种植园”的模式。众所周知,这位利华休姆勋爵(Lord Leverhulme)在当时的比属刚果建立了棕榈油工业,为他在利物浦的肥皂工厂提供原料,结果导致数千名刚果人死亡或失去土地。他创立的公司——利华兄弟公司(联合利华的前身)目前所使用的原料主要来自东南亚的种植园。
东南亚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居民特别容易受到这些种植园所引发的问题的影响。有些人可能欢迎种植园带来的经济机会,但还有些人却会遭受破坏性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例如,一旦森林被油棕所取代,沙捞越的本南族人(Penan)就再也找不到食物或干净的水了。在围绕棕榈油的讨论中,需要要考虑到这些不同的观点,避免重蹈殖民主义覆辙。

传统上讲,“狩猎采集者”是指不从事耕种,而是在特定的区域内过着流动的生活,以狩猎和捡拾野生植物获得食物的人群。但是,这个定义并不准确。如今,许多狩猎采集者不止是靠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可能有时还参与现金经济来补贴生活。比如,在种植园中打零工,从事休闲农业或园艺工作,为游客担当向导或搬运工,或销售森林产品和手工艺品等。由于环境恶化,包括油棕种植园对热带森林的破坏,让他们常常不得不以这些方式来维持生活。在退化的环境中,很难找到能提供充足和多样化饮食的动植物原材料。
但是,并非只有在发生大规模毁林的地区人们才会被迫采用这“多种经营”的谋生方式。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东南亚,许多狩猎采集者都在通过其他活动补充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种植园的不断入侵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些广泛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比如由于狩猎采集者通常流动性较高,非常依赖特定的生态系统,他们可能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棕榈油产业的某些特定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都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19世纪棕榈油产业引入该地区以来,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远?
土地权利的不确定性
油棕种植园对小农户的影响很好理解。他们迫于压力成为棕榈油生产商,但是高昂的化肥成本和大笔的前期资本投入导致他们很难经营下去。那些被大型棕榈油企业并购的小农户常常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收购方的发展规划更偏向于集约化的种植园,这些种植园使少数权益人群受益,而小农户则有可能沦落为种植园的无地劳动者。在印度尼西亚,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一代人的流离失所和经济发展的停滞。
但是,由于狩猎采集者经常过着游牧的生活,相比于小农,他们对土地权利的主张比较不明确,往往也更难获得当局的认可。
狩猎采集者通常与他们居住的土地有着极其深厚的联系。即使那里没有砖瓦房这种明显的“土地使用”标志,对他们来说,这些土地与森林也仍然充满了记忆和生活意义以及谋生的机会。尽管狩猎采集者也会在土地上做许多永久性标记,但他们的土地标记形式繁多,有时是引发联想的个人化地名,有时是动物踪迹的表述,有时则是常走的路径或者记忆中昆虫和鸟类的鸣叫地点。
尽管与祖先的土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但狩猎采集者通常没有土地权。东南亚地区土地确权方面的法律未能赶上2007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2007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的步伐。例如,为了给基础设施和采矿项目让路,菲律宾阿埃塔族(Agta)的狩猎采集者被迫搬迁。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即便土地权利得到承认,也很少将狩猎采集者觅食和狩猎的区域完整地包括在内。

这些土地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殖民时期制定的政策。在1948年到1960年期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the Malayan Emergency)之后,新成立的马来西亚政府延续了殖民地的有关土著人民长居土地权利的法律。这些法律受到了英国和战后反共产主义革命政策的影响,往往从安全利益出发对土著人民的权利多加限制。在沙捞越,英国人认为土著居民使用土地是一种“浪费”。今天,由于狩猎采伐者群体仍未获得土地权,当土地被油棕巨头侵占时,他们很有可能面临被驱逐的风险,从而失去为他们遮风挡雨,维系他们生存的森林。
人身威胁和环境恶化
就业是狩猎采集者被卷入棕榈油行业后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在各种小农、移民工人和土著社区中,油棕行业糟糕的用工模式为非法交易、生存依赖和债役等问题创造了条件。最近,一名39岁的孟加拉国移民工人因坠入棕榈油厂的废锅炉而死亡。国际组织报告指出,印度尼西亚工人在处理危险化学品时经常缺乏正确的防护设备。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没有国民身份和政治边缘化可能意味着他们特别容易遭受到这些危险。这样一来,大公司就更容易不受监管地雇佣他们,而他们获得的薪资、合同和条件也同样无法受到监管。即使他们选择不在种植园中劳作,而是留在森林里或森林的边缘地带,新的道路或其他项目也有可能让他们暴露在风险之中,以及随之而来的骚扰和虐待。
而且,东南亚地区还面临着土壤退化、化肥导致的水污染、森林大火等油棕种植园扩张引发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给狩猎采集者带来的影响格外严重,而且也是欧洲广播电视媒体最关注的问题,不少反棕榈油运动经常以受威胁的猩猩作为报告切入点。例如,法国备受争议的“能多益巧克力酱税”(Nutella tax)引起了棕榈油生产国的愤怒。作为回应,东南亚国家持续强调“可持续”棕榈油对健康和环境的好处。

油棕种植造成的森林砍伐和相关环境问题让居住在种植园附近的狩猎采集者更加难以在森林中找到食物和清洁的水源。因此,这些群体有时只能靠从商店购买廉价、不易腐烂的食物来维持生存。菲律宾的研究表明,当狩猎采集者被迫迁入这类定居点后,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会恶化。在马来西亚部分地区,棕榈油导致土著民族祖先传下的森林大规模流失,迫使狩猎采集者不得不搬到质量糟糕的政府安置区内,而且那里几乎没有就业机会。他们很难在这些森林遗迹中捕猎和采集食物,同时锰矿开采和种植园农药流失造成的污染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影响。2019年瓜拉岛(Kuala Koh)百特地区(Batek)发生的一起多人丧生的案件终于将这些问题暴露在世人眼前。
联合利华(Unilever)等公司及其在东南亚的供应商强调,他们会遵守承诺,避免侵犯人权,确保公平的雇佣模式,保证受影响群体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避免破坏环境和森林砍伐。但是随着棕榈油行业的不断发展,并逐渐成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核心产业(或许也是狩猎采集者自身的主要谋生方式),这个行业和对其进行部分规范的自愿认证机制就尤其需要遵守这些承诺的目标,从而避免殖民时期种植园里那些对人和生态都具有破坏性的制度再次回潮。这一点可以,而且也应该得到落实。而重视东南亚狩猎采集民族复杂且有细微差别的权利和愿望就是实现它的重要途径之一。
翻译:Est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