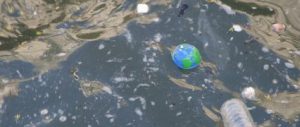遗址静静地藏在丛林深处,大片的石头建筑成了藤蔓的天下,它们盘根错节地缠绕在神庙、宫殿和金字塔上面。内部的密室被野草和丛林动物占领,曾经的道路也长满遮天蔽日的桃花心木和雪松。
这就是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古城蒂卡尔。曾几何时,这里的居民数量高达数万。至今依然耸立的宏伟纪念碑、充满溢美之词的碑文,甚至还有专门的球场,从建筑到城市规划都体现着当时人们无限勃发的雄心。
而今天,这里已经变成蜘蛛猴和美洲豹的天下。 “已经湮灭的城市里,到处都是浮雕、金字塔、神庙,人类的想象力至此已经穷尽。羽翼的扑动声逐渐渺茫,消失于无边的沉默之海。”危地马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写道。
达到极盛的巅峰后不久,曾经雄踞西半球最领先地位的玛雅文明在公元八世纪前后迅速衰落。一个个王国灭亡了,纪念碑变成齑粉,偌大的石头城空空荡荡。现在的蒂卡尔,已经变成一个崩溃的失败社会的象征。然而,崩溃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个问题长期吸引着学者们的关注。类似《古代玛雅:雨林文明的兴衰》的书籍堆满了相关人士的书架。
小说电影也从此汲取了素材,最近的代表作就是梅尔·吉布森的《启示》。中美洲这个湮灭的传奇有着一种绝对无法抗拒的诱惑。
最近的情况给玛雅研究抹上了一丝不和谐的色彩,这是一种焦虑甚至是不祥的预感。严肃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追问着一个乍听起来很荒唐的问题:玛雅的命运是否会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气候变化和全球金融危机是不是预示着我们的体制要走向扭曲变态和崩溃?
当然,没有人认为华尔街的高楼大厦上会缠满藤蔓植物,也不是说那些穿着细条纹西装的银行家会在曼哈顿大街上被吼猴追着屁股跑。当年犯错的玛雅的国王们,会在祭祀仪式上受到黄貂鱼骨刺穿阴茎的折磨,然后变成祭品。这实在是道德风险原则的一个加强版应用。在我们的时代,唯一会大量失去的就是奖金而已。
但是,玛雅的衰落和如今我们的危机惊人地相似。“我们认为自己是不同的,但实际上,过去所有的强大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就在他们行将崩溃的时候仍然这么想。”美国进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说。他还说,当玛雅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它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正处于巅峰。随着股市曲曲折折地拐入未知地带,随着冰盖持续融化,戴蒙德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评论家的响应。
那么,玛雅的故事意义何在?我们从中又能吸取哪些教训?戴蒙德在论文中指出:玛雅的人们建立起一个非常成熟先进的社会,最终却被自身的成功所摧毁。玛雅的人口增长很快,自然资源的消耗超过负荷底线。政治精英无法解决不断加剧的经济问题,最终体系崩溃。这个崩溃根本不需要洪水瘟疫之类的外部原因。毁灭玛雅的就是一种环境导致的温水煮青蛙式的危机,领导人没有及时发现并予以解决。
“随着人口、财富、资源消费和废物产量都达到巅峰,环境影响也会最大(这是资源能够承载环境影响的极限)。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社会总是在达到巅峰之后就迅速崩溃了。”这个观点是戴蒙德在2003年的著作《最后的美洲人:环境崩溃与文明终结》中提出的,在他的新作《大崩坏》中又有所扩展。
环境、经济和政治压力之间的联系非常清楚,戴蒙德认为:“如果人们都绝望不堪、饥寒交迫,他们就会埋怨政府无能,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
尤卡坦半岛包括了从墨西哥南部到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伯利兹的广大地区,然而在半岛上的丛林遗址之旅却是一次苦不堪言的经历。湿热的天气如附骨之疽,成群的蚊子又叮又咬。玛雅并不是印加和阿兹特克那样的统一帝国,而是一系列纷争不断的王国。玛雅文明的第一批聚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世纪,但是人们所熟知的“古典”时期要晚得多,大约到公元250年左右才开始。而最后阶段(丛公元750年到900年的极盛和衰落期)则被称为“终极古典”时期。
蒂卡尔古城位于危地马拉北部佩腾的丛林深处。这里是玛雅的首都之一,城里不规则地布满了石灰岩建筑,当年居住着足足10万人。国王身兼最高祭司和政治领袖二职,城市周围拱卫着刻有象形符号的卫城,还有平顶的金字塔,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们在塔上描绘了星座图和计算周密的日历。
这些宏大工程完全是靠人力建成的。玛雅人没有牛、骡子和马等帮助拖曳推拉的牲畜,就连用水也是有限的,全都要依靠降雨。截至公元750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已经达到数百万,大部分都是农民。由于王公贵族的攀比奢华,纪念碑和宫殿越造越华丽,然后一切开始急转直下。考古记录表明,纪念碑的建造突然中止,上面铭刻的溢美之词也没了下文。还有证据表明宫殿可能遭到过焚烧。
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这里的居民消失了。在短短几代的时间里,玛雅的人口从几百万锐减到几万、甚至数千人。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城市,迁往北方,留下来的人则出生率暴跌(在数学上,俄罗斯人口的减少与此类似)。等16世纪西班牙人到达这里的时候,玛雅人已经不见踪迹了。如今,茂盛的植被重新覆盖了蒂卡尔,把一切都染上了绿油油的苔迹,但是那些神庙——前哥伦布时代的最高建筑仍然高耸于丛林之上。美国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在拍第一部《星球大战》时,曾经把这里作为义军基地的拍摄地。
为了解释玛雅文明的神秘衰落,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原因,包括外敌入侵、疾病蔓延、商路改道、严重干旱等等。但是,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是:衰落的首要原因在于环境压力。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马赛罗·卡努托指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被拉伸到极限”。湖泊淤塞,地力枯竭,尽管耕种和人工水库增加了水和食物的供应,但人口增长还是超过了技术创新的解决能力。
尽管玛雅社会结构复杂而井井有条,但它却是温水煮青蛙的一个典型例子。卡努图说:“一切都在系统内酝酿着,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政治精英们终于开始做出反应了,他们向神灵奉献更多祭品,对邻国进行掠夺,这种反应只是让情况变得更糟。“王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产生了一种涟漪效应。他们没能对危机作出正确的应对,在事后诸葛亮的我们看来,这场危机实在是一清二楚的。”
环境问题是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部分被降雨模式和粮食产量的短期波动所掩盖。但是当引爆点到来时,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他们成功的基础实在太脆弱了。国王们保持威信、防止动乱的办法就是仪式和献祭,如果他们很明显无法做到这些时,人民就会失去信心,整个王权系统也就会分崩离析。”《古代玛雅的衰落》的作者戴维·韦伯斯特说。
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的类似情况。韦伯斯特透过他在宾州大学办公室的窗子,注视着这个冬季的第一场降雪,他一直在等待这个问题的到来。在办公室的墙上,钉着一张关于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的旧剪报。“那就是第一次震颤,”韦伯斯特沉思着说,“你知道,每当事物在看起来最成功的时候崩溃,人们总是觉得很吃惊。我们傲然四顾,觉得自己国富民强、英明睿智、安居乐业,绝对没想到自己已经站在某种危险的边缘。是傲慢吗?不。是无知。”
一些人类学者难以把古代和现代社会直接联系起来,他们觉得这超出了学术范畴。但韦伯斯特不这么想。“和玛雅一样,我们在自身对世界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上不太理性。玛雅人有他们的祭祀和祭品,换句话说就是魔法。我们也相信魔法,相信金钱和创新能让我们超越自身系统的内在限制,而旧的规则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
近来这种观点很流行,然而在八十年代的股市繁荣和九十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它被看成胡思乱想的卢德主义。当时,“宇宙巨人”们横行华尔街,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中大力欢呼自由经济精神的胜利。借用星球大战中的话说,那个年代已经和遥远星系中的久远时间一样遥不可及了。现在,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已成为历史,各国政府都在忙着接管银行、扶持市场。
如果我们把商界人士和他们所谓“证券化”、“衍生性金融商品”等费解的行话比作在神庙里念咒的玛雅祭司,那乔治·W·布什和戈登·布朗就是那些倒霉国王了。他们不但没有对“魔法”提出质疑,反而对“祭司”们进行煽动。当布朗还是财政大臣的时候,他曾经对这种“魔法”进行保护,2004年他说过:“在预算内外我都希望我们能对冒险者进行更多的鼓励。”现在“魔法”的缺陷已经暴露了,我们听到的也不再是电影《华尔街》中戈登·盖柯的名言——“贪婪是好的!”,而是诗人雪莱《奥西曼提斯》中的句子:“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寂寞平沙空莽莽/伸向荒凉的四方。”
耶鲁大学的卡努图把玛雅看作一个前车之鉴。当年玛雅的国王们坐视危机失去控制,他们显然不是补救危机的合适人选,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竟然把投资扔进了已经破败的系统。“你不会想让那些危机的制造者来解决危机的,”卡努图说。由于时间上的巧合,布什已经开始走出这个泥潭,但布朗和其它八国集团国家的领导人还在原地徘徊。
有几位评论家认为,和即将到来的生态飓风相比,这场金融危机不过是一场小暴风而已。欧洲的一项研究估计仅森林破坏造成的自然资本损失就相当于每年2-5万亿美元。乔治·蒙比尔特十月在《卫报》的一篇文章(该文同时在中外对话上发表)中写道:“两种危机的原因是相同的,……两种情况下,资源开发者期待的回报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造成的损失也无法弥补。同时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断然否认可能发生的后果。”蒙比尔特指出,由于生态是所有财富产生的基础,金融和环境危机是互相促生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玛雅的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玛雅的人口膨胀就像一辆越开越快的汽车,直到引擎爆炸,”韦伯斯特说,“拿我自己来说。我今年65岁,当我出生的时候,世界人口只有20亿,现在已经接近70亿。这实在非同小可。”最后,稀缺能源的压力将完全压倒技术,玛雅这样,我们也是这样。“西方式的自负让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并把这称为进步,”韦伯斯特说着,声音低沉下来:“我很高兴自己不是三十岁,我实在不想看到四五十年后的情形。”
和服装的底边一样,“大决战”对风尚的变化十分敏感。关于这一主题的电影已经拍了一大串(比如《惊变2天》和《我是传奇》和《盲流感》),这些电影中所假想的世界比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想象还要残酷得多。戈马克·麦卡锡的后启示小说《长路》被当作一个环境寓言而大红大紫,它也将被拍成电影。他在写到烤制“婴儿肉串”的食人者时描绘道:“沉落的太阳环绕着地球,就像一位提着油灯的哀伤的母亲”。韦伯斯特并不认为情况会坏到那种程度,“不会像(电影)《疯狂的麦克斯》里演得那么糟糕,但绝对不会怎么愉快。”他尽力用显得很愉快的声音说。
这种沮丧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报道过去已经被一再热炒,但是经过马克思、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石油危机的众多时代,资本主义都顽固地活了下来。与玛雅相比,我们的技术还是有可能抵抗住人口和环境的双重压力的。马尔萨斯主义的乌鸦嘴们大大低估了技术在提高粮食产量上的能力,包括改良灌溉、杀虫剂、粮食新品种和其它技术。人口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可望在2050年前达到92亿的峰值并开始下降。《经济学家》承认,亚洲国家正在越来越接近西方膳食和消费模式,这会加快资源的枯竭。但是不必紧张,因为“人类的智慧永无止境”。
如果这个悲观的环境预言是正确的,全球变暖将拉开一场大浩劫的序幕,我们又有什么机会做出比玛雅人更好的应对?2000年获选的是布什而不是戈尔,这体现了在选择“国王”上智慧的有限,遭到削弱的《京都议定书》也许就和烧掉玉米祭神一样合情合理。当美国共和党人念叨着“钻!宝贝,钻!”的时候,把他们比喻成赤脚穿套头连衣裙寻找下一个牺牲品的家伙,恐怕也不算什么曲解。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大有希望的兆头。各国政府开始赋予森林等“自然”资产货币价值,这一概念上的飞跃可以大大促进经济。欧盟已经建起一个碳交易市场,促使工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正在推动一项新的气候条约,各国政府每年将付给热带国家数十亿美元,以保持其森林的完好。厄瓜多尔提出,只要每年获得3.5亿美元的资金,就不开发亚马逊地下的10亿桶石油。“我相信21世纪将是自然资本的时代,就像金融资本支配了20世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说。
即使如此,难道就够了吗?文明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多种多样。如果能从中美洲的废墟中吸取一条简单的教训,那就是:保护环境并控制人口。这是迈克尔·科的观点,他在1966年发表了极具发展眼光的论文《玛雅文明》。他还说:“没有文明能永远存在,大多数都在200到600年之间。”玛雅文明、罗马文明和柬埔寨吴哥王朝的存续时间都是600年。
那么我们的文明呢?“西方文明开始于文艺复兴,到现在刚好600年,”科说,“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选择,可以让情况变得更糟,也可以改变它们。这正是科学的作用。但是这需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意愿,”这位世界最杰出的文明衰落研究专家之一停顿了一下,说:“说句实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拥有这种意愿。”
来源:www.guardian.co.uk
卫报新闻传媒有限公司2008年版权所有
首页图片由Yogi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