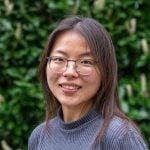今年7月,北京郊区的一家自然教育基地在夏令营期间突遇暴雨,随后发生的山体滑坡和断电导致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度被困。工作人员没有等待外部救援,而是立即组建了一支应急小组,监测水位、评估撤离方案,并通过雨水收集、柴火灶、光伏发电和直流水泵等方式,在几日内保障了基本生活。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去找政府,而是立刻自发组织应急措施。由于及时安装了光伏设备,他们成为村里最早恢复供电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室研究员郑艳对这个细节表示印象深刻。这家教育基地在暴雨中的自发行动,体现了中国社区内部自组织力量正在应对气候风险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今年9月,中国宣布了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专家告诉对话地球,中国公众正切身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缺乏明确而有效的途径参与气候适应行动。
直接参与
中国于 2013 年出台了首个《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但直到 2022 年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中才将“公众参与”正式纳入政策目标。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环境政治学者沈诗然表示,“气候减缓政策能够依赖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行业治理,但气候适应则具有本地性和紧迫性,必须引入公众参与,才能真正落地。”
然而,普通民众如何能够参与气候适应行动?她发表的最新论文把目光投向了由人民网运营的“领导留言板”——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的政府留言板。
领导留言板于2008年正式上线,目前已覆盖中国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民众可以使用该平台举报地方治理不善、请求行政支持或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尽管该系统旨在涵盖广泛的政策议题,但它已日益成为公民表达对气候相关风险的渠道,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
2021年7月,河南遭遇罕见特大暴雨。连日暴雨导致严重洪灾,近400人遇难,1400多万人受灾。
沈诗然分析了2021年1月1日至10月4日的所有留言,发现洪灾发生前,河南省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洪水的留言,而洪灾过后,洪水过后,呼吁改善排水系统、升级基础设施和保障社区安全的请愿数量急剧且持续增长。“这些信息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气候变化,但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防洪的诉求。”她说。
沈诗然还指出,社交媒体的帖子一般用来反映个人情感或公众舆论,而政府运营平台上的留言往往是面向政府的正式呼吁。她说,留言板为公民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渠道,让他们可以表达与治理和公共安全相关的具体诉求。
她的研究还发现,河南洪灾带来了跨省的溢出效应。从2021年7月17日至10月4日,河南省外的有关气候适应的留言约有67条,其中13条明确指向了“河南洪灾”。
一位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的民众在留言板上写道:“今年夏天,成都也将迎来暴雨,我想咨询一下,成都地铁是否做好的应对极端天气的措施,尤其是类似郑州地铁倒灌的情况下?”
沈诗然指出,公民提交查询时,个人需选择主题类别,并指定目标政府部门回复,相关部门则被要求公开回应。她正在进行的研究不仅会考察地方政府在该平台上的回应方式,还会考察反复或协调一致的公众呼吁最终是否会影响正式的气候适应政策。
激发社区内部的力量
尽管领导留言板表明,公民的气候意识不断提升,并在灾害发生后积极参与应对,但有效的适应措施仍依赖于事先的主动参与。非政府组织和大学生志愿团体为此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他们的工作侧重于长期能力建设,提升当地气候知识水平,并支持社区制定自身的适应策略。这些努力有时可能会影响政策,但更直接的影响体现在社区内部:居民开始自发组织,制定应急计划,并建立即便缺乏外部援助也能持续运作的应对策略。
去年,北京大学环境与地理学硕士吕杭洲就利用 “大学生团队与在地组织结对子”的方式,在云南、江西、陕西等地共同开展了气候风险评估与本土知识调研。
大学生们负责收集和整理数据,而非政府组织则协助联系当地社区并动员他们参与其中。调研完成后,研究结果反馈给了当地组织,由他们继续带动社区落实适应行动,例如修缮防涝设施、建立互助网络、储备应急物资等。
吕杭洲在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的组织下参与编写了《农村社区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指南》,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农村气候风险调研培训体系。最开始该评估方法的培训工作坊只面向社会组织开展,但实践发现,社会组织在人力、数据分析与电脑技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大学生志愿团队的加入,正好起到了互补作用。
这些大学生通常在项目地驻扎一周左右,进行田野调查。只要不耽误农活,村民们往往非常乐于交流。“他们在休息或闲暇时,会热情地聊天、分享故事,甚至请学生到家里做客。”吕杭洲分享道。不少学生团队在调研同时还会通过社交媒体记录所见所感,将气候行动与公众传播结合起来。
吕杭洲的职责是远程提供指导。虽然远隔千里,他说自己“仍能感受到,那些学生真正在融入当地、理解当地——而这正是我们理想中的目标。”
在具体的调研过程中,团队并不会简单地发放调查问卷,而是引导村民共同讨论。例如,村民们围坐在圆桌旁,面对村庄地图,一起标注当地河流、农作物分布、易涝或干旱区域等。绘制资源图能够帮助民众可视化风险认知。
他们还会绘制“农事日历图”,标注各季节的生产活动,讨论气候变化是否打乱了原有节奏。这种参与方式让当地居民有机会分享自身的经验,从而发现问题并提出可能的应对措施。
研究团队则会引入气象数据,分析降雨、温度等指标的变化趋势,并将这些量化数据与村民提供的经验信息进行比对。最终形成的报告既包含科学数据分析,也融入了村民的本土知识与建议。
吕杭洲说:“很多解决方案并不是外部专家想出来的,而是在村民的交流中自然形成的。”他还补充道,大学生与社会组织的角色,是搭建沟通的平台,让社区的“内生力量”被激发出来。
一些研究成果会反馈至政府层面,转化为政策建议。例如,江西的一位村长在项目结果的启发下,调整了村庄排水规划。
然而,吕杭洲认为,更重要的成果发生在社区内部。 “我们希望公众不是被动等待政府改善,而是在社区内部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他说。例如,一些村庄开始组织青年与老年人的“一对一互助小组”,为老人编写极端天气安全手册;在干旱地区,社会组织则协助农户建立起了应急储水系统。
用创新迎接挑战
尽管全国各地已经有了一些社区实践,但要让大众的气候适应行动规模化、制度化,并不容易。要激发更多自下而上的气候适应行动,郑艳认为需要三个条件:稳定的政策土壤,持续的资金支持,以及社会组织的创新和自我造血能力。
最直接的限制仍然是资源与持续性。吕杭洲表示,他仍在推广“社会组织+大学生合作”进行农村气候风险调研的模式,但他坦言:“去年组织项目的时候,我们经费非常紧张,很多大学生都是自己垫付路费。”社会组织的处境也类似, 资金不足成了他们之间最常见的共识。
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在资助体系中存在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部分原因是前者更容易量化与核算,后者则往往难以用数字体现成效。
根据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简称CPI)2021年的报告,中国具有减缓效益的行业获得了1.3万亿元(1,930亿美元)的资金,占总额的60%。其中55%用于风能和太阳能行业,而与适应相关的项目获得了560亿元(83亿美元)的资金,仅占气候金融总额的4%。其余资金则用于“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等具有间接减缓和适应效益的活动。
此外,致力于在农村展开气候行动的非政府组织常常感到不知从何入手。专注于可持续食物与农业的非营利组织食通社发表的报告指出,一些带着气候资金进入乡村的机构往往发现,问题的根源并非气候本身,而在于当地长期存在的民生、基础设施、医疗和老龄化问题。这让许多社会组织陷入两难:他们既想回应气候议题,又不得不从更基础的民生层面重新出发。
尽管困难重重,郑艳认为,气候适应议题为社会组织创新带来了新的可能。她指出,部分基金会和公益机构正在尝试调整方向:不再要求社会组织“改赛道”,而是引导他们思考“我+气候”的结合方式,从教育、健康、农业、灾害管理等领域出发,嵌入气候韧性思维。
她强调,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气候适应政策框架体系,提出适应和减缓同样重要。但是在社区层面,真正能长期发挥作用的,是内部形成的行动力,而非依赖外部救助。“无论是妈妈志愿团、青年社群,还是社区基金会,他们才是气候适应的未来。”郑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