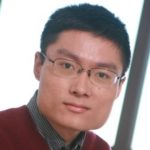对于中国环境气候领域的观察者来说,过去的一年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并不为过。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宣示的碳中和目标启动了中国气候政策的密集出台的进程。新的低碳目标、政策、法规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迅速成型、接连公布。碳中和目标宣布后的两个月,更新的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在“雄心峰会”上提出。然后在今年三月的“两会”上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包含了一系列气候和能源2025年目标。
气候政策制订并未止步于“十四五”规划的出台。正当外界指出“十四五”气候能源目标理应更加进取之时,“两会”刚刚闭幕就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使人们意识到“十四五”规划目标很可能只是在为未来五年的低碳雄心“筑底”而远非“建顶”。
在出席一场7月举办的论坛时,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透露,一套详细而完整的“双碳”目标政策体系(“1+N”政策体系)正在制订中。这套指导中国未来四十年去碳化进程的政策体系中的“1”指的是一份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顶层指导意见,“N”则包含了30多个涉及碳达峰、碳中和的全国和各地方、各领域、各行业的政策措施。
但2021年7月更为人所铭记的可能是河南乃至整个华中地区遭受的严重洪涝灾害。7月20日至21日之间的24小时,郑州降雨量达到了惊人的622.7毫米,接近通常年份全年平均降水总量。灾害造成河南全省数百人死亡和失踪。
尽管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在本轮暴雨灾害的后期通过主流媒体的报道有所呈现,但也有一部分网上的声音认为华中和华北的多雨是一种“瑞兆”。降雨线大幅向北移动意味着“大陆国家的盛世来了,” 一篇流传甚广的网文写道,“或许,汉唐时期那鼎鼎有名的河套平原,能让我们这代的中国人重新目睹。”
对上述网文的作者来说,气候变化对中国是一件好事。这样内容的广泛传播和“喜闻乐见”促使生态环境部旗下的官方媒体《中国环境报》发表专题报道进行驳斥。通过采访多位中国气候科学家,这篇报道力图说明严重的气候变化对于西北和华北地区来说远远谈不上“福报”。气候变化对于大气环流的影响加剧了宁夏、山西、甘肃等省份部分地区的干旱,又同时使得其它地区面临更极端的暴雨洪水的侵袭,西北本就是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该地区如要达到南方类似的湿润程度,需要极大的气候变迁才能实现……这对人类社会很可能是大灾难,而不是机遇或机会,” 该报道采访的专家表示。
这次交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存在的重要矛盾点。一方面,中国有对气候议题极为重视和态度严肃的领导层,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对气候议题表现出模棱两可态度的公众,后者对于各项低碳政策整体上采取一种默认和跟随的姿态。而2021年,当低碳行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并且越来越“动真格”时,社会不得不直面这些政策的真实影响和效力,其对于去碳化进程的接受度也受到检验。
几乎与河南暴雨同时,今年夏天的中国能源市场出现了紧张的迹象。伴随着工业和出口的强劲复苏,激增的电力消费使煤炭供应吃紧,煤炭价格升至十年高位。高涨的煤价显著增加了下游电力、钢铁等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宏观经济运行。7月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一系列旨在稳定能源市场的精神,其中包括对于“运动式减碳”的叫停。一些评论将“运动式减碳”解读为在新的能源基础设施尚未就位的情况下过早地对于煤炭相关能源基础设施“釜底抽薪。”
这是自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首次出现的明确政策调整信号。但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却存在各种不同解读。对于能源市场监管者来说,它意味着短期内一些曾经受控的煤炭产能可以释放以稳定煤炭供应和价格。另一方面,控制高污染高耗能的“两高”行业的力度却丝毫未减。对环境监管者来说,这些能耗大户对电力的占用在电力紧张的背景下更应得到控制。
但一场“电荒”已箭在弦上。9月末,多省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在东北甚至出现了影响居民用电的大停电。
与“梦回唐朝”式的气候变化否定论比起来,电荒引发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之辩对于中国气候政策走向的影响要深远得多。“电荒”刚冒头的时候,就有一些报道和评论将其与中国多年以来用以推动节能减排的能源“双控”政策挂钩,认为是“双控”加码导致一些地方不得不采取拉闸限电方式应对。然而,后续研究和分析则显示“双控”政策并非本轮限停电的根本原因,在部分省份对于高耗能行业的限电措施恰恰是“电荒”的果而不是因。本轮电荒折射的更多的是中国电力市场在价格、传输等机制方面存在的不畅,而它在舆论场上的喧嚣则使得“双碳”政策承受了大量舆论压力。
这场“电荒”之辩发生的时机颇为敏感。“1+N”政策框架原本应在九月末的时间窗口正式公布,为11月初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前几周密集的气候外交定调。从9月开始,中国面临的国际气候外交压力就明显增加。该月初,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就造访天津与解振华见面,并通过视频方式与多位中方高层官员和领导人沟通。克里前脚刚走,英国COP26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也降落天津与中方会面。
没有几项中国国内的政策议程像气候政策一样,与国际外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在过去的几年呈现出强化的趋势。有中外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在气候议题上承担起领导者和国际公共品提供者的角色,可能有助于提升“绩效合法性”。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是在联合国大会这一场合率先宣布的,新的2030年气候目标是在英国主办的“雄心峰会”上揭晓的,而克里在今年四月访问上海也为习主席出席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铺平了道路。在这一峰会上,中国宣布了煤炭消费达峰的时间点。当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逐渐临近,人们自然而然会关心,中国是否会以这一场今年国际气候外交的重头戏为契机来公布新的国内气候政策。
9月底的联合国大会表明,国际舞台确实仍然是中国重大气候政策的“宣发地”。在联大的视频讲话中,习主席宣布中国将停止新建海外煤电项目,并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低碳能源。这一宣示在国际上收获如潮好评。有报道指出,它是克里和夏尔马访华时与中方沟通的事项之一,前者还曾提议中国将碳达峰时间提前。但除了“海外退煤”承诺之外,中国没有在联大提出新的国内气候政策目标。十月份终于问世的“1+N”政策框架主要包含了过去一年所宣布的既有政策目标。
到了这一阶段,中国气候政策的重心似已转为巩固和夯实已有的气候行动及步调,而不是加码新的目标和承诺。中国的官员和专家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现有的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已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沉甸甸的国际担当,用时远比发达国家实现同等目标所需时间要短。 COP26大会之前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也很难说有利于国际协同提升气候雄心。在“1+N”政策框架中首次出现了气候变化的“对外斗争”提法,并与“对外合作”并置,显示领导层对于国际气候政治的更冷峻的判断。这种情绪也在中国互联网上有所体现。对于西方气候倡导声音的高度怀疑使得“气候环保议题是外部势力压制中国发展企图”的论调再次甚嚣尘上。
在能源安全顾虑和对西方“寸步不让”的舆论氛围中,中国的气候雄心和目标没有因此缩水或回退,已经值得瞩目。2020年9月以来所宣布和制订的主要气候目标全部原封不动地进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意见,通过“1+N”政策框架正式成为国内顶层政策。中国气候政策制订需要保持的平衡性也在COP26气候大会上得以充分体现。例如,中国没有加入美欧所主导的《全球甲烷承诺》(该承诺包含了一个十年内减排30%的量化减排目标),而选择在与美国共同发布的联合宣言中对下一阶段的甲烷控制行动做出表态和安排。“美欧等急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施压,并转化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来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的研究人员对《中国环境报》记者如此评价《全球甲烷承诺》。在格拉斯哥所达成的中美联合宣言表明,中国对于治理甲烷这一强力温室气体是有意愿和决心的,但需要根据自己的步调来安排减排行动。
今年春天,当我们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时,他曾提醒海内外的中国气候行动关注者们,“十四五”等近期目标任务固然重要,但更要考虑未来四十年的路径怎么走。实现碳中和将是一个系统性结构性的转型过程,是“长征”而不是短跑。其他中国专家也认可这一提法,他们认为中国应用接下来几年为碳中和准备和搭建系统性的基础,否则即便提前几年达峰了,后面也很难实现碳中和。在COP26大会期间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王毅仍觉得外界没有充分理解中国的这一重要的政策取向:”为了实现我们的(双碳)目标,我们所勾画的是对整套系统的变革方案,这个变革并不仅限于能源系统,而是涵盖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如果长期的系统搭建比起取悦外界的短期减排目标更重要,那么COP26大会之后的中国气候领域并没有因为国际大会的结束而沉寂。中国人民银行在十一月推出了低碳支持工具,向金融机构释放大量流动性用以降低低碳产业的融资成本;新的中央深改委会议精神也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一改革直指造成“电荒”的一些根本性症结,也将为新能源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但是相比起简单直接的控排承诺,这些政策措施很少进入国际媒体的视野。对于中国来说,要让外界接受“行稳才得以致远”的气候行动哲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