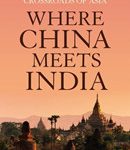中国人必须调整的核理念,不仅仅只局限于要保证已建、在建核电站的长期运行的“绝对”避免福岛事故,还需要保证核电站所产生的大量高放射性核废料有一个妥善的保存方法,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剩余的长寿命放射性核废料,在其生存期间(可能是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绝对”不会污染环境和地下水。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需要澄清一种观念是,核事故之所以要制止,原因决不在于死了多少人。要看到核事故的出现,是可能影响到子孙万代生存环境达几万年、几十万年的事故,决不能拿核事故中的死亡人数与飞机失事、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作对比。
那些支持发展核能的专家总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来说事:平均每发TWeY(1012瓦年)电能的即时死亡人数,核能只有8人,相比于煤的342人、天然气的85人以及水电的883人是最少的。但实际上他们这样的比较是非常不科学的,是应该批评的。
其实,美国的核政策就没有解决好后处理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人在核废料的处理上,所奉行的是“一次通过”的方针。所谓“一次通过”就是设法将核废料做成玻璃体状态(因为玻璃体状态有憎水性,在水中的溶解度极小),然后存放到某一由不锈钢制成的盒子里,填放在地下。据说,已有的待填存的库即将爆满,并且温度已上升到200多度。但美国仍有近8万吨的核废料有待处置。
在核废料后处理方面,比较先进的是法国和英国。这两国不仅已能从核废料里有效地提出钚,而且已将钚制成Mox燃料。俄罗斯、印度和日本也实施了一些有限的重新处理活动,美国计划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一个Mox燃料站。Mox燃料是既可充作快堆,又可供应慢堆 的核燃料体系。其差别在于天然铀和钚的比例不同。但是,虽然Mox燃料的制作和生产技术都已成熟,却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解决了剩余的强放射核如何“放置”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我们至今尚无明确的对策如何存储未来的核废料(虽然有计划将中国西部变成亚洲再加工的中心)。
与此同时,如何看待快速反应堆优点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虽然它可以有效利用铀资源,可以解决“燃料短缺”的问题,但反应堆的设计逐渐变得更有难度,同时在印度等国也提出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中国已制定了大发展快堆的规划,要在2050年弄出4~5亿千瓦,主要是快中子堆的核电站;但发展的准备工作却远没有做好,技术比日本、印度均落后很多。中国的核科学家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快堆蕴含着巨大的核安全风险。
所有这些有关核安全的方针问题,都未明确回答,也没有技术准备,但是工程院咨询报告,就提出一个“大跃进”的规划。这太危险了!
在如何确保核安全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战争的破坏和恐怖分子的袭击。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制定国际公约,即一旦发生两国之间或多国之间的战争,作战各方均不得袭击对方的核电站。凡是决定袭击对方核电站的决策者,不论其战争胜负如何,一律由国际社会追究决策者破坏人类居住环境的罪责。
至于恐怖分子的破坏活动,这类国际公约恐怕毫无约束力,因此我们只能依靠更多的国际合作来抑制他们的活动。同时,中国在已建、在建核电站的管理上,必须尽量减少核恐怖分子袭击中国核电站的危险。对于“后处理”工厂、Mox燃料的生产设备也要采取同样的措施。
我还认为,中国的核政策不应以“慢堆、快堆、热核堆”作为近期发展的目标,也就是中国的核能主要不是为近期发展服务,因为大发展的条件并不具备。既然如此,我为何要认为核能应该被大力推广呢?
我赞成中国的核能主要不是用来做基本电力,而是用来解决海洋航运问题。我赞成扩大建造核潜艇,大力发展核航母。核航母的建造,不仅要确保核动力的稳定持续和突然变动的供应,也就是核功率可大幅度变动,还要防止对方导弹和鱼雷的破坏和袭击。一座有充分保护的大型核动力装置显然有助于提高技术,也有助于学习到如何有效地抵御战争破坏和防止恐怖分子袭击。尤为重要的,万一遭到破坏,所污染的是海水,不是陆地上的水源和地下水。
核动力也应该被应用在远洋航行的大吨位航船上。中国的船舶工业已居世界第一位,其产值以及对远洋运输的贡献,至为巨大,但动力却严重地依赖石油。如果要维持这一巨大产业的持续的能源供应,最好改为由中型、大型的核动力来驱动。
我也支持将核电站做成可以海上移动的反应堆,以调节某些地区突然发生的电力的不足。
最后,我很赞成适当发展小型的电、热两用的核电站。尽管这类小型核电站的热电转化率较低,但比大型核电站更安全,余热还可用来解决居民的供暖、供冷、供炊等问题,以促进城市建设的清洁化。
所有这些我都支持,但我绝不赞成现行的将核电作为基本电力的大发展的方针。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
本文图片来源:U.S. Army Garrison Humphre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