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伦酋长领地(Malen Chiefdom)坐落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旁,距离塞拉利昂南部普杰洪区(Pujehun)首府90分钟的车程。过去十年,这里的景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地区典型的原始林地和自耕农场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上万公顷的油棕。
同样经历巨变的还有这里的和平和宁静。油棕给这个西非偏远的角落带来了暴力和纷争。直到今天,土地引发的冲突仍在继续。心怀愤懑的当地人声称,他们的土地在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没有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被夺走。与此同时,位于冲突中心的种植园企业却从世界主要的可持续棕榈油认证机构“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那里获得了广受觊觎的认证。
这一切都始于2011年。这一年索芬农业公司(SAC)与塞拉利昂政府和马伦地方权力机构——酋长领地理事会签订了一份为期50年的土地租赁协议。SAC是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农业产业跨国公司索芬集团的子公司。根据最初的协议,SAC租赁的土地面积为16249英亩(约合6576公顷)。但接下来的几年中双方又签订了若干补充协议,大大增加了SAC的租地面积。纸面上,SAC目前获得了18473公顷土地的特许使用权,占马伦酋长领地27000公顷总面积的近70%。非营利组织GRAIN的数据显示,目前其中12349公顷土地种植了油棕,是塞拉利昂正在运营的最大的油棕种植园。
十年冲突
这笔土地交易从一开始就纷争不断。在租约签订后不久,不少当地社群成员就指控其非法。2011年10月,这些人组织起来的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Malen Affected Land Owners Association,简称“MALOA”)致信政府,称租约是在缺乏透明度或未与本地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商讨的情况下达成的,并且土地租金“少得可怜”、“不可接受”。这封信还指控租赁协议背后最大的推手马伦大酋长、酋长领地理事长维克托·凯比(Victor Kebbie)收受了SAC的贿赂,威逼土地主签约。
同月,围绕土地租约的紧张态势升级为抗议示威,100多名土地主封堵了通向SAC特许经营区的道路。按照美国智库奥克兰研究所(Oakland Institute)的说法,当局逮捕了40人,并以“暴动行为、密谋和威胁性言语”(riotous conduct, conspiracy, and threatening language)的罪名对其中15人提起了诉讼。
此后,局面持续恶化,直至2019年1月2名男子在暴力冲突中中枪身亡。从一开始就关注这场冲突的当地非政府组织“绿景”(Green Scenery)在相关调查报告中声称该事件中存在侵犯人权的情形,并警告称“全副武装的军警”在酋长领地“随意逮捕”和“过度使用武力”已经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恐怖气氛”。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FIAN比利时分部的信息,多年来出现过诸多解决冲突的尝试,但迄今无一成功。2018年,塞拉利昂总统朱利叶斯·马达·比奥(Julius Maada Bio)在竞选中承诺会化解冲突——他当选后的确履行了这一承诺,成立了一个调停委员会。委员会展开了调查,并在次年提交了一份17页的报告,支持了当地社群对SAC和马伦当局的诸多指控,包括确认了SAC事实上的特许经营区面积比纸面上的18473公顷多出了650多公顷。尽管这份报告的泄露版本可以在网上找到,但截至目前官方仍未正式发布这份报告。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和支持该团体的非政府组织认为,政府目前尚未采取任何措施回应这份报告。而最近的一次调停努力也同样收到指责,它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出资支持的一个为期两年的和平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在这次活动显然未邀请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参加之后,该团体再次表达了不满。
加入RSPO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12月,该种植园及其榨油厂获得了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RSPO的初步认证。这意味着马伦种植园生产的所有棕榈油现在都被认证为可持续产品。换言之,这些棕榈油都被认为满足了RSPO的《原则和标准》——这是棕榈油行业内部用来衡量可持续性的一套内容广泛的标准。这些标准的核心便是尊重当地社区和人权,包括将土地改作油棕种植园时应获得土地使用者的“自由、事先的知情同意”(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并对土地使用者的权益损失予以合理的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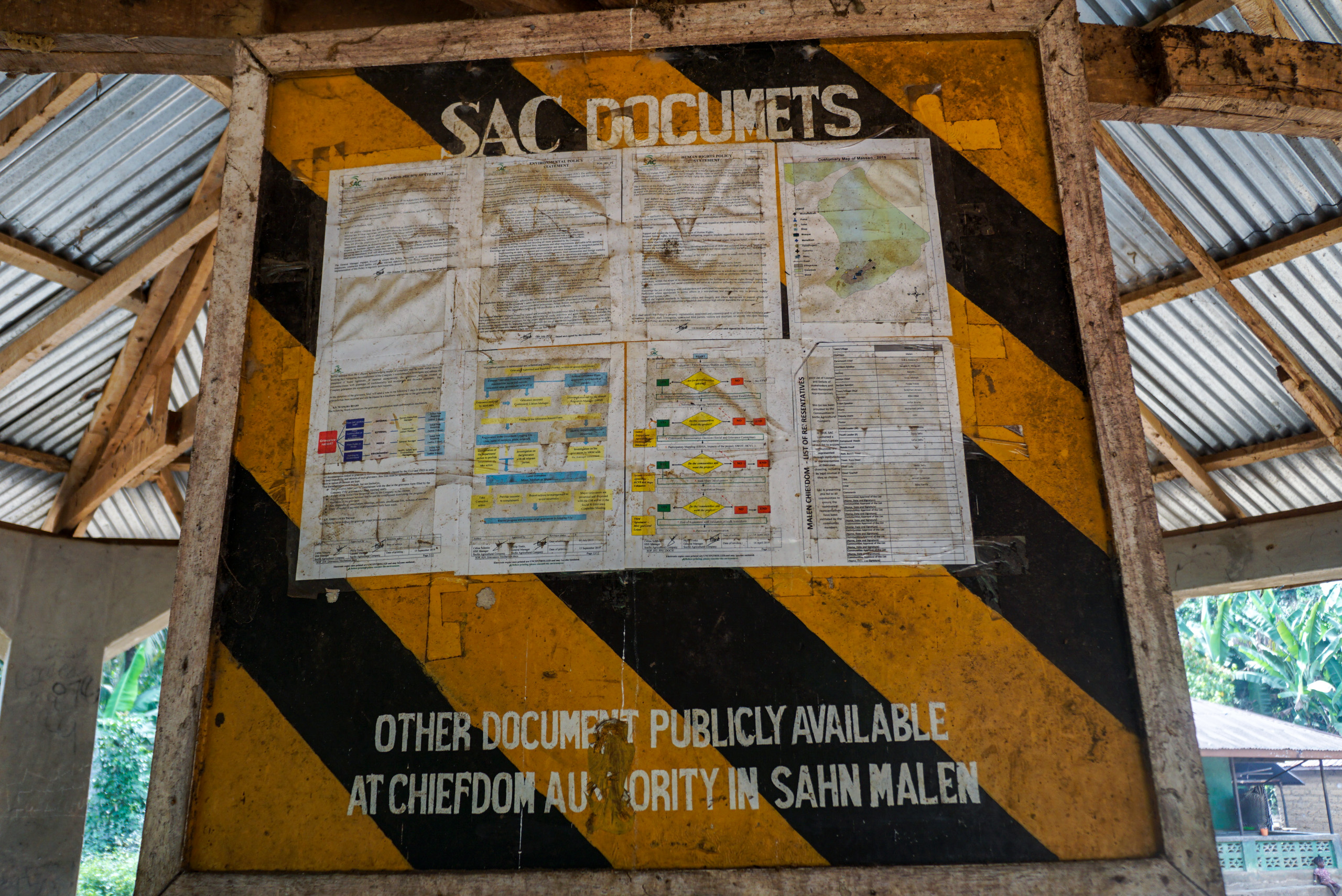
为了获得认证,SAC经历了漫长的审计过程——包括2020年下半年由第三方审计公司SCS全球服务公司(SCS Global Services)对种植园进行的两次实地考察。SCS全球服务公司的报告今年2月才在RSPO官网上发布。其中显示,SCS全球服务公司的团队在审计期间与包括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在内(尽管该团体似乎否认此事)的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会面。报告记录了会谈期间各方提出的不满。但在最终的结论中,SCS全球服务公司仅列出了关于该土地冲突的三项违反RSPO原则的“观察”(observations)。一般认为,“意见”不过是“审计团队的笔记”,而其纠错行动则是“自愿性的,不会影响认证的结果。”
更多信息
SAC的RSPO认证和审计报告请访问:https://rspo.org/certification/search-for-certified-growers,搜索“Socfin Agricultural Company”。
审计报告列举了四项“重要的违规事项”(critical nonconformities),如果不改正将无法获得认证。截至去年年底获得认证时,SAC已经对其中三项进行了改正。唯一未改的事项是在未对土地的生态保护价值,或碳汇价值进行评估的情况下便清理土地。SAC获准在12个月内找到修正或者补偿的办法,否则将被吊销认证。审计报告指出,RSPO对SAC对改项工作的“投身”抱有信心。但同时,RSPO否决了SAC迄今提出的所有补救方案。对SAC来说,似乎在塞拉利昂找到补救方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该公司最近的一份提案是关于一个在喀麦隆的项目。
鉴于时间紧迫,再加上这个难点问题充满争议,SAC很可能将在今年年底失去刚刚获得的可持续认证。

“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别无选择。”
马伦土地交易与SAC的到来给当地人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影响,不止冲突暴力本身。
如今被SAC掌控的土地在种满油棕之前曾是马伦当地人的主要食物来源。FIAN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描述,当地社群曾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一系列营养丰富的食物”,甚至是在土地休耕的时候(轮作是塞拉利昂一项非常普遍的农业生产实践,通过休耕可以恢复土壤肥力)“仍是柴火、野味、野生植物、蜂蜜和草药的来源”。报告指出,失去这些土地对于酋长领地的粮食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连那些获得了补偿金的居民也受到了影响。哈瓦·克洛玛(Hawa Koroma)是一位居住在海尼村(Heinie)的寡妇,60岁出头,独自供养着八个孩子。2012年,她将土地租给SAC的时候得到了200万利昂(约合460美元)的一次性补偿。她用这笔钱支付孩子的学费,购买瓦楞铁板修补漏雨的屋顶,很快就用完了。她每年还会收到大约2万利昂(目前约合1.5美元)的租金——但这根本无法弥补她失去土地、不再能够种植粮食供养家人的损失。如今,她主要依靠在后院种菜以及在房前走廊上支起小木桌出售食用油、香烟、饼干和其他零食维持生计。

除了土地之外,克洛玛还失去了一项在塞拉利昂乡村被认为至关重要的资产:她的油棕树。油棕是西非的原生物种,那些有足够土地的家庭往往都会自己栽培油棕,并使用传统手工工艺榨取棕榈油。棕榈油在这一地区的饮食和文化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并且对粮食安全和草根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克洛玛以前可以出售富余的棕榈油,但现在已经无法以此贴补家用了。
不过对于克洛玛来说,她还遭受了更大的不公。她说,自己家从前有4英亩(约合1.6公顷)土地,但SAC自行丈量后只向她支付了2英亩地的补偿款。塞拉利昂乡村地区很多地块还没有得到清晰的测绘,而按照Mongabay采写的一篇文章的说法,传统上土地有时“以大树枝这样的东西划定边界”。即便带着世界上最好的意图,像SAC这样的公司带着一个测绘队进场,也很难把边界搞清楚。在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看来,这给“严重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让SAC得以“通过输入错误数字”的方式欺骗土地主。
即便土地划分公平公正,克洛玛仍然坚称,如果她可以选择的话,一定不会租出土地。“要么出租土地,要么有可能钱地两失。我们是被迫签约的。我们别无选择,”她说。
克洛玛之所以感到别无选择,原因部分在于马伦的酋长理事会和最高酋长维克托·凯比。在塞拉利昂乡村,最高酋长拥有巨大的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该国管辖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根据法律顾问帕特里克·N·约翰布尔(Patrick N. Johnbull)对马伦交易的分析,自从“原住民部落对土地的所有权”在殖民时代得到认可以来,当地乡村就确立了社区或者家庭拥有土地的制度。但由于这种所有制的集体属性,土地被认为是由“部族当局”代表集体持有。根据塞拉利昂现行土地法,“部落当局”被定义为“最高酋长及其顾问或显要人物,或者副酋长及其顾问或显要人物”。
事实上,各酋长领地的情况各有不同。根据活跃在当地的德国世界饥饿救助组织(Welthungerhilfe)的案例研究,在马伦,最高酋长就是土地的“最高托管人”,是土地权分配中的核心人物。除此之外,按照Mongabay的说法,维克托·凯比还是塞拉利昂最有权势的最高酋长,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像克洛玛这样的土地主会感到自己不得不就范。
硬币的另一面
那么,马伦的最高酋长为什么要将自己领地上超过70%的土地交给企业建设油棕种植园呢?酋长领地议长山普贝·罗伯特·莫伊古阿(Shempbe Robert Moiguah)给出了一个答案:发展。“此前马伦有很多茅草屋,但现在非常少了,人口也有所增长,状况良好的道路也增多了,”他坐在自家屋檐下半睡半醒地说。莫伊古阿坚称,SAC将长期在此经营,而酋长理事会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该公司履行对当地社区的承诺。
SAC公司将很多这些承诺以“社区发展行动计划”之名列入了其2011年的《环境、社会与健康影响评估》——这份评估报告是取得在塞拉利昂经营所需的环境许可证的前提。FIAN在其2019年的报告中分析了2011年到2017年间SAC为这些计划支出,发现其承诺的金额与实际兑现的金额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差距之一存在于SAC的小农户合同农业计划。根据该计划,当地农民可以将自家种植的油棕果卖给SAC。SAC曾计划在2014年到2025年为这一项目拨款782.4万美元。FIAN发现,直到2017年这笔钱并未实际使用。
不过也有一些承诺已经兑现。SAC在铺设和维护种植园周边道路上花的钱超出了原本的计划。虽然SAC自身显然从中受益,但这也的确也方便了当地人出行。SAC在开挖水井和修建学校等社区项目上的投入也显而易见。

种植园给马伦带来的就业机会也确实令很多人受益。“在这家公司工作对我是很好的,”SAC雇员易卜拉欣·阿玛拉(Ibrahim Amara)表示。“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很难养活家人。”阿玛拉的工作是采摘棕榈果以及打扫种植园。他用挣到的钱盖了一间房子,并且还能供孩子们上学。尽管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等组织指控SAC种植园工作条件恶劣,但仍有很多人排着队希望成为SAC的员工。



SAC的到来还引发了涓滴效应,给当地社区创造了就业。穆罕默德·凯塔(Mohamed Keita)是一个裁缝,在马伦的主要城镇萨恩(Sahn)经营着一家店铺。2015年,SAC与他签订合同,委托他为该公司员工制作工服。“我每年大约制作500套工服,收入约为1000万利昂(目前约合750美元),这一切都要感谢SAC,”他说。
“现在他们开始污染我们的水源了”
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都对这笔土地交易的利弊进行了详细的审视。但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是SAC的到来给马伦的环境带来的影响。
当地人不仅失去了他们曾经赖以为生的农场和林地,还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RSPO的审计报告显示,除了为了维持种植园生产力而每年施用的大约100吨化学投入品之外,种植园里的榨油厂也是污染源头。这座榨油厂建于2015年,预计今年可以生产超过4.5万吨毛棕榈油。

2019年一份针对土地冲突的政府报告显示,由于种植园特许经营区没有设置缓冲带,因此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据FIAN估算数量达到惊人的逾3.2万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SAC的《环境、社会与健康影响评估》和RSPO的《原则和标准》都强调,种植园周边应设立缓冲区或者绿带。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当地社区不受农药等污染物的伤害,也为了保护水域、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


53岁的渔民赛莱拉·莱比(Salia Lebbie)一辈子都住在马萨奥村(Massao)。这个小村子坐落在马伦河沿岸、SAC榨油厂下游1.5公里的地方。莱比所在的社区不论是饮用水,还是食物,以及交通和盥洗都离不开这条河。
“我从小就知道这条河就是我们生计的来源。我在这条河里学会了钓鱼和划船,”莱比说。如今,人们不再有过去有那么多土地种植花生、木薯、豆子和其他作物了,所以这条河就变得更加重要。“我的家庭的生存全靠这条河,”他说。
但这条河的状况却并不好。莱比说,“河水有时候会变成棕色,有时还能看到死鱼漂在水面上”。他清楚其中的原因,认为这都是由于SAC的榨油厂在排放废水。这些废水有一部分是通过废水处理池外溢间接排放的,还有一部分则是直接通过管道排入河流和湿地。“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现在又来污染我们的水源,”他说。
紧邻榨油厂的柯图马汉村(Kortumahun)情况同样糟糕。当地居民表示,榨油厂废料散发出的恶臭让他们不得不捂住鼻子。他们还担心潜在的健康风险,抱怨蚊子太多,晚上根本没办法坐在室外乘凉——他们认为,蚊子来自榨油厂的污水处理池。
去年12月,34岁的农民悉迪·斯瓦雷(Sidie Swaray)的两个孩子患上了疟疾,这让他备受打击。他说,每逢雨季(每年5到10月)情况就更加严重,痢疾和霍乱病例会增加。

柯图马汉以南约30分钟车程的宏盖村(Hongai)设有一个由两位医务人员值守的小型社区卫生站。负责卫生站的护士约瑟芬·严库巴(Josephine Yankuba)表示,他们为包括柯图马汉和马萨奥在内的河流沿岸社区的约2000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严库巴确认,疟疾、霍乱和痢疾在雨季确实多发,但她同时指出,现在即便是在旱季(每年11月到次年4月)病例数也居高不下。去年9月到12月,单是痢疾,卫生站就接诊了69个病人,并且其中很多是儿童。严库巴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缺少清洁的饮用水,很多患者都抱怨他们的河流被SAC污染了。
“关于污染,我们一直大声疾呼。我们甚至向环境保护署提出了正式的申诉,”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协调员基尼·詹姆斯·布兰戈(Kinney James Blango)表示。他告诉中外对话,政府机构已经进行了调查,但受影响的社区至今还在等待调查结果。
棕榈油让人人受益?
SAC说它来到塞拉利昂的原因之一是该国国内棕榈油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其官网称,塞拉利昂人均棕榈油消费量为每月1公斤,传统的手工压榨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导致2019年“当地市场消费的棕榈油中有50%来自进口。”
SAC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塞拉利昂所有棕榈油消费都与食用相关,但实际上这是具有误导性的。欧盟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价值链分析报告认同塞拉利昂存在“食用棕榈油总体短缺”的问题。但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大量棕榈油被用来生产肥皂,出口给西非其他市场。这样看来,SAC自我标榜的“成为本国市场上主要的棕榈油供应商”的目标与支持塞拉利昂的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尽管该公司承认,塞拉利昂“在粮食生产国排名中垫底”。



实际上,棕榈油这种在塞拉利昂被看做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显然处于短缺状态,这一点从其居高不下的售价上便一目了然——目前1品脱(约0.47升)棕榈油的售价可以达到6000利昂(约合0.45美元)。加上塞拉利昂的通货膨胀率是全球最高的(过去10年该国棕榈油价格上涨了三倍多),棕榈油已经成为了一些消费者买不起的商品,特别是在该国超过半数人口每天仅靠不到1.25美元维生的情况下。
只有那些自己拥有油棕树的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市场压力的影响。在马伦,一小群扛住了SAC种植园扩张压力的土地主便是如此。
博卡利·兰达(Bockarie Landa)与妻子和五个孩子住在SAC种植园东北方向一个依然被森林环绕的小村庄扎奥(Jao)。兰达拥有大约3公顷土地,包括一个小型的油棕种植园。他从未后悔当初保住了这块土地,但能保留下来却并非易事。如果不是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的支持——该组织很多成员都多次遭到逮捕,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当初就不可能顶住酋长领地理事会的压力。如今,兰达和村子里像他一样的乡亲们再次开始反击——这一次他们要争取的是经营自己的农场的自由。
“他们不允许我们自己加工棕榈油。他们试图阻止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自己加工棕榈油,就能赚到足够多的钱,也就不需要为他们工作了,”他说。
博卡利不得不偷偷加工棕榈油。他在林中一个隐秘地点生产棕榈油,然后用独木舟把它偷运到市场上。“否则,他们就会把这些油全部没收,以盗窃公司油棕果的罪名逮捕我,”他说。博卡利所在的村子里还有其他人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据他们说,有些村民之前曾被逮捕,不得不在缴纳巨额罚款与被扔进监狱之间选择。
未来会怎样?
SAC近期成功取得RSPO认证使其在马伦的种植园更多了一分长期的确定性。它的油棕树已经成熟,而企业也已经实现了在塞拉利昂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的计划——尽管SAC宣传的3027个岗位中有一半都不是长期就业机会,而是“日结工”或者外包雇员。不过简而言之,SAC不会离开。即便是对SAC不乏微词的2019年政府报告都默认了这一点。报告称,各方均认同,“企业应该在一个包容、互相尊重、信任和互利的环境中继续经营”。

SAC和它的18473公顷种植园与本世纪最初几年以来试图在西非和中非其他地区发展油棕种植园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外国企业争先恐后地来到这片“新前沿”收购土地。连锁反应研究(Chain Reaction Research)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事情并未如计划的那般顺利,“企业获得的特许经营区面积与最终建成的工业化油棕种植园面积之间差距很大”。这些项目之所以会失败,原因之一便是广泛的社区抵抗。
那么,为什么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等群体不屈不挠的反对却未能阻止SAC扩张的脚步?一个原因是政府参与到了土地交易中。把索芬集团请到塞拉利昂的是政府,与马伦酋长理事会签订土地租约的也是政府——SAC只是与政府签订了转租协议,并没有直接与马伦当局签约。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马伦可以在各种指控和抗议的漩涡中仍然能够相对保持淡定的原因。不过他们仍然试图引导舆论,并对绿景这样受到它的诽谤指控的组织采取法律行动。马伦受影响土地所有者协会的布兰戈认为,或许这也正是政府对污染和补偿不足的投诉基本都视而不见的原因。

布兰戈表示,他所代表的土地主们希望拿回他们的土地。如果拿不回来,他们希望SAC可以坐下来和他们重新商定租约的条款。“我们不是针对企业。我们想要的不过是公平、诚实的交易。我们不能接受在企业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我们这些土地主却像这样饱受艰辛,”他说。
阅读中外对话棕榈油系列文章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