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中规定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义务。2016年,该法修正案第一条摒弃了“利用”一词,改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国内外批评者对修订后的法律仍然不满,认为新法仍然包括了一些为老虎养殖和其他商业行为提供了法律基础的条款,而这会刺激对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无论其合法与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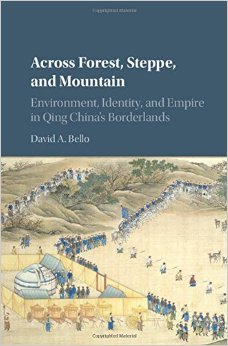 对人类和野生动植物的关系进行反思,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时间不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球正面临着第六次(而且是第一次人为因素造成的)物种大灭绝的观点已逐渐成为科学共识,于是那些把野生动物单纯作为一种资源而超出“合理利用”范畴的行为也开始面临压力。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2016地球生命力报告》用数字印证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灭绝的严重程度。据其估算,以1970年的种类数量为参考值,世界三分之二的野生动物都会在2020年之前灭绝。
对人类和野生动植物的关系进行反思,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时间不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球正面临着第六次(而且是第一次人为因素造成的)物种大灭绝的观点已逐渐成为科学共识,于是那些把野生动物单纯作为一种资源而超出“合理利用”范畴的行为也开始面临压力。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2016地球生命力报告》用数字印证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灭绝的严重程度。据其估算,以1970年的种类数量为参考值,世界三分之二的野生动物都会在2020年之前灭绝。
人们已经越来越切身地体会到自己与动物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如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所体现出来的,人们正对这种相互依存的概念进行深入的再思考。我们可以从这个新角度回顾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中国人与动物关系的演变,而这会令我们对今天中国的生态状况和政治体制都能产生新的认识。
在统一了中原和亚洲内陆(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后,清帝国获得了比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大的的疆土。这片广袤土地容纳的人文和生态多样性是新中国继承的一笔重要的环境遗产。
如果没有十七世纪中期满清南下入关,今天的中国不会拥有如此辽阔的国土。但人类的战争掩盖了亚洲内陆地区人与动物之间的战争:正是要围猎那些不想被捉住的动物,满人才成为了剽悍的骑射民族。
从猎人到战士
清军开疆拓土的军事技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大量练习围猎积累而来,而猎场往往延伸到当时的国境线以外。
要培养和传承满洲弓马骑射的技能就必须进行围猎,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绥远将军补熙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奏折。他担心,如果不进行围猎,年轻的士兵们就会丧失弓马骑射之技。但是,只有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才具备围猎所需的场地和野物。与补熙出征的中国南方不同,那里野兔、狐狸和羚羊仍然满布于野。傅恒希望带着他的部队参加每年一度的秋狝,因为“若只操练而无狝猎,则难以弓马娴熟。”
游牧者的“经济特区”
满、蒙地区的游牧技能是人与动物数千年的相处累积下来的。清政府顶住了汉族移民的压力,勉力维持这种游牧生活方式,从而难得地保存了农耕文明无法容纳的人类多样性。清政府对游牧者的保护不仅包括调停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在草原发生天灾时对牧民予以赈济。雍正十二年(1734年)冬,暴雪冻死了七成牛羊,正是清廷的钱粮赈济拯救了数千家乌拉特部众的生命。数年后,一份乾隆六年(1741年)的上谕体现出清政府对游牧生活方式危机的认识。文件指出,惟赖朝廷钱粮维生恐非长久之计,游牧者原有的生活方式必须有所改变。
清政府出于战略原因而努力维护草原上的人畜依存关系。在新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这种依存关系直到今天仍然维持着。如今中国正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找到解决草场退化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同时解决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带来的问题,但采矿已经成为威胁畜牧业的新问题。
败给了蚊子的清军
除了人与牛羊的关系,蚊虫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清帝国的国界。比如,携带疟疾的蚊子让大波易受感染的汉族移民远离云南的荒僻地区,那里直到今天还存在致命的疟疾——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多样性受汉族影响最小的地区。直到1900年前后科学研究才揭开蚊子与疟疾之间的联系,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疟疾的区域分布才被人类认知。
疟蚊阻止了清朝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这一地区的政治和人口局势也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766-1769年间,乾隆帝派精兵强将征缅。然而,在两国战争中,他的精兵却由于疟疾而伤亡惨重。1780年,乾隆帝不得不宣布停止征缅。因此,当地的土司制度比中国其他地方维持的时间都要长。汉人移民与当地人之间对疟疾抵抗力的强弱差异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
笔者的《山河之间:清朝边疆地区的环境、身份认同和帝国》是一部环境历史著作,从21世纪的视角阐释了17到19世纪人与动物的关系。本书聚焦于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历史意义,特别是这种关系怎样深刻地影响了满洲、内蒙古和云南等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足迹。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