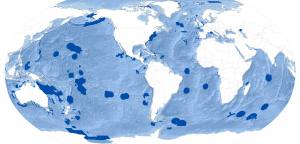牦牛在这片终年大风的高原上悠哉游哉的生活着。有时一眼望去,我能看到上千头牦牛。被藏民奉为神鸟的黑颈鹤也在中国西部青藏高原的这片边缘地带繁衍生息。这里海拔3400米以上,是黄河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湿地之一。尽管这里的湿地修复工作成绩斐然,但除了牦牛和黑颈鹤这些见证者之外,鲜有人注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川北部广袤的若尔盖草原上曾因错误的建议挖掘了很多排水沟。如今,这些排水沟已经被填堵上了。泥炭沼泽的“复湿”对自然和牦牛牧民来说都是好消息。牦牛作为一种长毛耐寒动物,在这片并不宜居的土地上繁衍壮大,不仅为人类提供牛奶、牛肉、牛皮,而且可以作为运输工具,粪便也可用作燃料。
但当地生态学家认为,目前,这一地区的牦牛数量太多了。
面对城里人对牦牛产品的旺盛需求,牧民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可是,他们又被告知为了维持草原的恢复,必须减少牦牛数量。当地政府的处境很微妙——既要维护若尔盖的生态系统,又要让西藏的牦牛文化存续下去。

火车上拍摄到的牦牛群。图片来源: Yuriy Rzhemovskiy/Unsplash
大干涸
若尔盖草原面积2.7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厚达10米的泥炭沼泽,这些沼泽为数百万头牦牛提供着给养,对全国的水文也至关重要。若尔盖草原泥炭沼泽位于长江和黄河这两大河流的源头,旱季时黄河上游45%的水都来自这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提高若尔盖的畜牧能力,人们在这里挖沟排水,开沟达700多公里,导致若尔盖沼泽地区的水位降低了近50%,给这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这些排水沟引发了一场生态危机。随着水位下降,茂盛的草原被旱生植物所占据,涌入排水沟的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土壤侵蚀。草原上的17个湖泊中有6个完全干涸。这里的沼泽就像海绵一样,过去一直不断地给黄河提供着稳定的补给,而后来变得高峰期流量增多,关键的旱季流量却减少了,从而给黄河两岸华北粮食产地直至入海口的供水带来了威胁。
湿地大修复
由于担心发生水文灾害,在总部位于荷兰的“湿地国际”等国际环保组织的谏言下,中央政府开始介入草原管理工作。1999年,政府下令禁止进一步排水,并设立了包括若尔盖国家自然保护区在内的5个自然保护区。负责这里大部分监管工作的四川湿地管理中心的顾海军说,2004年开始填堵排水沟后,若尔盖草原逐渐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湿地恢复项目所在地,恢复高原湿地面积约64平方公里。
1月的若尔盖之行让我看到了许多成功修复的区域。那些排水工程的小型水坝几乎都被新的泥炭和及膝高的植被淹没,草原上最大的湖泊——花湖的面积已经增加一倍,达6.9平方公里。
藏族人鲁克(音译)11年来一直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守护花湖。他在岸边告诉我,花湖重新焕发生机引来了鸟类的回归,这里也日益成为夏季旅游胜地。他还说,夏季湖边聚集的200多种鸟类,最令人激动的是,其中黑颈鹤的数量占全球总量的十分之一。

若尔盖自然保护区内的黑颈鹤。(图片来源: Dave Curtis)
鲁克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在这里筑巢的数千对黑颈鹤。黑颈鹤已经成为当地保护活动的标志。当地乡镇的很多建筑物都以其形象为装饰,数量之多一点也不亚于当地大量的传统天然标志物——牦牛角。
以牦牛为中心的生态系统
随着工作的深入,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称,全面恢复若尔盖需要的不仅仅是封堵排水沟。虽然牧场状况有所改善,但大家的观点都很一致,那就是牦牛太多了——目前的数量是50年前的4倍。
问题是多少才算太多?“这取决于你问谁,”顾海军说。
一些环保主义者想让牦牛彻底从这里消失。“保护区最初的想法是彻底停止放牧来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国家自然保护区副主任永秀(音译)说。但现在的想法又不同了。一项在200公顷的围挡区内进行的为期3年的禁牧实验表明,禁止放牧可能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围挡区看起来很壮观,即便在冬天也长满了披碱草这样高大的草类,但它们挤占了矮草、药草和莎草的生长空间。其中,莎草经常被黑颈鹤用来筑巢。“我们需要牦牛来维持生物多样性,”永秀总结说。
外国湿地生态学家对此表示认同。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汉斯·朱斯滕表示,生态系统不可能回到没有牦牛之前的状态。几千年来的牦牛放牧和踩踏已经让沼泽草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结果是出现“一片被认为是美丽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新景观……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开放景观之一”。
“牦牛是藏人命之所系”
目前保护区内每公顷土地上平均有超过10头牦牛和羊,是估计承载力的数倍。这一数字应该减少多少目前还没有答案。永秀说,生态可能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文化也很重要。
“牦牛是藏人的命,”她说。“牦牛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一切。牦牛角是我们身份的象征,是藏传佛教的圣物。牦牛意味着地位,现在仍被视为财富的标志。”

西藏的牦牛牧民。(图片来源: Matt Ming)
草原上的地方政府希望为牧民提供其他生计,旅游就是其中之一。红原县有一个大型游客中心,每年8月都会举办牦牛音乐节。这里曾是1935年红军长征路上一个重要的落脚点,游客可以走上瓦切湿地的木板路,沿着“红军长征体验大道”走一遭。县里还在沿路设立了一些摊位,牧民们可以在这里为游客提供牦牛奶、骑马等商品和服务。
牧民还有机会成为护林员。红原县雇佣了1000多人,负责巡逻发现草原上的入侵者、维护围栏、以及照顾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也在做同样的事。
我就遇到了一位护林员。尚特(音译)是个地地道道的藏民,穿着御寒的传统藏袍,外套的长袖子几乎垂到地面,即便不戴手套,双手也不会受冻。尚特说他家还养着50头牦牛,但也提到他热爱自己照看的野生动物:藏羚羊、在草从里玩耍的幼狼以及在“他的”溪边住着的6对黑颈鹤。
往日不可能重来。现在大多数牧民都骑着摩托而不是马去照料动物,住在城镇边缘的房子里,而不是帐篷里,他们的孩子会上学,很多还上了大学。
市场力量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养牦牛可以赚钱。一头4岁的健康牦牛卖肉能够赚大约750美元。中国城市居民喜欢瘦牦牛肉和酸奶等乳制品,这些被认为是绿色有机食品。
牧民最清楚
永秀相信,修复泥炭湿地的方法是延续和适应西藏的文化传统。她说:“我们需要在保护和生计之间取得平衡,怎么实现牧民最清楚。”长期从事该地区牧场管理研究的耶鲁大学人类学者高煜芳说,牧民给了他信心。
上世纪80年代政府推行农业集体化改革,若尔盖草原上的放牧权下放到牧民个人。他们用围栏把原先开阔的草场变成了一个迷宫。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让草原深受其害。集体农业草原优化利用的方法已经丢失,高煜芳说。
我开车穿过草原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围栏的两边,一边因过度放牧而光秃秃的,另一边却牧草茵茵。这种隔离对环境和牧民而言都没有意义。
牧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好几个牧民把牧群集中起来,并且拆掉围栏。一些政府官员也支持这么做,高煜芳说。
我离开时,西藏的寒风愈发凛冽。在黄河上游的圣地唐克附近,一群牦牛走过激起尘土飞扬,不远处则有另一群在冰上踉跄着觅食。一边是充沛的水源,一边是不断逼近的沙漠,这种对比显得尤为奇特。
翻译: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