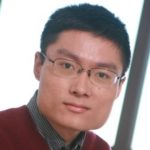整整一年以前,在江城武汉,张继先和李文亮等医务工作者正通过他们各自的方式对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发出警示。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历史中的重要一页。
站在2021年的起点,世界还是未能从新冠疫情的噩梦中醒来。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截止目前,疫情已造成超过180万人死亡,并仍在继续增长。虽然疫苗的研制获得了突破,但世界范围的接种之路注定坎坷。即便在2020年的最后几天,病毒也没有“休息”的迹象。在英国发现的新的变异毒株迫使多国关闭边境,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新的毒株会影响现有疫苗的有效性。
2020年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或许是应对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去年7月,一队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召集的全球人畜共患病科学家共同撰文指出,人类应对大流行病的惯常方式—在疾病爆发后通过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案加以扼制—比起通过消除疾病的诱因来预防大流行的发生要代价高昂得多。而流行病的一个重要诱因和驱动因素就是人类导致的全球生态环境变迁。
这些科学家指出,70%的新兴疾病,如埃博拉和寨卡,以及几乎所有已知的流行病(包括SARS和COVID-19在内),都是动物源的。抗击新冠疫情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使中国领导层下定决心重新定义人类与自然的边界。从武汉发生疫情之后的12个月,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年。密集出台和修订的法律法规如赛跑一般地去关上可能导致公共健康风险的漏洞和隐患。这些规章制度的修改也将从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未来命运。
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互动
1月,在全国上下认识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的同时,关于疫情与野生动物关系的激烈讨论也随之出现。中国公众对于2003年的SARS疫情记忆犹新,而那场疫情后来被证实与果子狸的消费有关。在关于疫情的早期报道中,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作为被怀疑的最早爆发地存在野生动物交易的事实与公众对于SARS疫情的惨痛记忆相吻合,同时也与科学界关于流行病的动物来源的猜测相匹配。尽管后来浮现的科学证据显示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并非新冠病毒的来源地(有研究指出病毒可能在到达武汉之前已在其它地区“静悄悄地传播”),但中国社会在2020年的最初几个月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野味消费”和“生态保护”的全民大讨论。

“为了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武汉封城一个月之后的2月24日,通过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与此同时,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法》(“野保法”)的全面修订也进入了快车道。
之后,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决定”的精神,通过了多个地方条例,使“禁食令”在省市层面落地。其中一些地方法规因为超越了“野生动物”的范畴(如囊括了宠物和养殖水产)而引发了广泛关注。
尽管这些立法动作迅速果断,但它们也呈现出了“救火”式的政策制订所难以避免的简单化倾向。食用野生动物作为最直接的公众健康风险得到了其应得的严肃对待。但这些新的法规对于其它的野生动物消费形式,如药用和皮毛等,却往往语焉不详。诚然,这些应用因为往往涉及灭活动物制品而具有相对较低的公众健康风险(野生动物入药的公众健康效应更为复杂),但是它们仍旧会增加人类不当接触野生动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应用为人类入侵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提供了经济激励。
中外对话去年4月对当时社会上几份重要的野保法修订建议进行的梳理发现,这些极具价值的建议在杜绝野生动物食用方面投注了大量注意力,但对于其它应用则相对着墨不多。一些外部观察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倾向。
保护和利用的拉锯战
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选择“食用”这个相对较窄的切入口有其道理。即便是在这个公众认可度最高的领域,“禁食令”也不得不面对一些回弹。要将长久以来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的人类经济、文化与野生动物分离开,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禁食令”甫一出台,就有大量媒体报道将野生动物饲养繁育产业的规模及其创造的就业呈现在公众面前。为了经济目的而饲养野生动物是中国很多生物多样性较高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且很多被饲养的动物并不属于濒危之列。成群被扑杀的竹鼠的影像传递的讯息是被毁掉的生计和失去的经济机会,这在一个疫情肆虐、经济受挫的年份来说尤其触动公众的神经。另一方面,国际上泛起的指责中国的声音使得中国国内更加难以开展开诚布公的讨论。一种更防御性的姿态开始显现。有的声音提出,禁食野味不就等同于承认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吗?
这种碰撞的最戏剧化的表达可能要数养殖户对生态学家提起诉讼,认为生态学家“对人工驯养野生动物从业企业和人员的社会声誉造成严重损害。”
如何将这一深刻反思转化为一套全新的法律准则、文化习俗和经济激励将会是中国社会接下来需要全力以赴解答的命题。
跨越2020年一整年的《野保法》修订将改写人与自然边界所面临的挑战呈现得淋漓尽致。全国人大的“禁食令”需要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和完善,而各方的争议最终体现在针对几份名单的“拉锯战”之中。这既包括了严格保护的野生动物”黑名单”,也包括了允许饲养繁殖和利用的“白名单”。
5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一份可食用动物“白名单”(即《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就是一次平衡严格保护和有条件利用的尝试。这份征求意见稿凸显了中国社会与野生动物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野生”与“家养”之间的模糊界限。比如,梅花鹿虽然位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因为“养殖历史悠久,已经形成完善的产业体系”而被加入“白名单”。马鹿同样作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入选“白名单”的理由则是少数民族饲养习惯。生态保护工作者表示可以接受一份有限的“白名单”从而换取更大范围的保护。但他们同时指出,确保市场上养殖野生动物的可追溯性是允许利用的前提,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防疫标准也应提上议程。
30%
土地用途的改变是催生流行病的重要驱动因素,贡献了1960年以来超过30%的新报告疾病。
中国领导层显然也意识到了野生动物产业转型所面临的挑战。7月,在广西考察“禁食令”和《野保法》执行情况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指出要区别情况,稳妥处理,使养殖场户有序有效转产转型升级。对于禁养品种要禁止继续养殖,有些要改为其他国家允许人工养殖的品种进行养殖;有的现有养殖品种被禁食后,可作其他国家允许的开发利用。
关于保护与利用的争论持续到了10月《野保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的时间点。尽管有专家仍在坚持推动限制和最终禁止对野生动物的商业性利用,但草案还是给非食用性商业利用留下了空间,并通过一套复杂的许可体系将这些利用框定在法律范围之内,尽管这套许可体系在过往也催生过各种“钻空子”的行为。
聚焦根本问题
当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法规修订吸引了大部分关注和眼球时,人与自然之间重新划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却在公众视野之外静悄悄地推进。
正如IPBES的科学家们所指出的,在世界范围内,土地用途的改变是催生流行病的重要驱动因素,贡献了1960年以来超过30%的新报告疾病。这些土地利用的改变包括森林砍伐、人类进入野生动物栖息地定居、粮食种植和牲畜饲养以及城市化等。
优化空间规划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是2012年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线之一。新冠疫情敲响了生态系统退化威胁人类自身安全的警钟。在因疫情而推迟举行的2020年“两会”上,11位人大代表提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在对该建议的答复中,生态环境部强调了中央政府扩大生态保护空间的决心。
作为这种决心的体现,6月,就在全国各地“解封”没多久,中国发布了《全国重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并提出到203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6%,湿地保护率提高到60%,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18%以上,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全面保护。

截止2019年底,中国已经将大约25%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红线区”保护范围。生态红线机制也被认为是中国利用空间规划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独特创举。2020年,关于生态红线管理的具体政策也得以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初步明确了生态红线区内可为和不可为的边界,澄清了一些之前存在的模糊地带。
这份11月出台的征求意见稿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红线内的地区不是“无人区”。一些受到高度管制的人类活动,如生计型的耕种和放牧,以及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开展。
生态环境部计划在2020年底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相比起公众投注在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上的注意力,在山川湖泊之间划定“看不见”的生态红线没有带来轰轰烈烈的全民热议。
人与自然之间重新划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却在公众视野之外静悄悄地推进。
但对于理解空间规划深意的人来说,这件事的重要程度绝对不容忽视。在9月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有针对生态环境部的问题提出将四分之一的国土划入生态红线区是否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对此,生态环境部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表示,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他指出,生态红线区内不是“绝对保护”,鼓励各地合理利用生态保护红线的优质生态资源,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中国雄心勃勃的生物多样性议程原本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昆明原定于10月举办重要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谈判,中国将作为主席国带领各国制订后202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这一切都已被推迟到2021年。
但也许正因如此,中国领导层能够从这场全球大流行中获得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启示。“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言时指出。
如何将这一深刻反思转化为一套全新的法律准则、文化习俗和经济激励将会是中国社会接下来需要全力以赴解答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