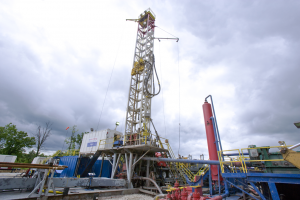1963年,中国在位于渤海湾、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大连蛇岛建立了第一个海洋保护区,保护生存在这里和附近海域的上万条蝮蛇;1980年,蛇岛和附近的大连老铁山一起被批准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chinadialogue_factbox title=编者按]
本文为中国海洋保护专题报道的第二篇文章,点击阅读第一篇文章《公海保护大谈判:难在何处?》
[/chinadialogue_factbox]
此后的近40年,中国近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开始了与经济发展的漫长赛跑。沿着中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各种大大小小的保护区被建立起来。截至2017年,中国海洋保护区面积近12.4万平方公里,占中国管辖海域面积的4.1%。
但各地热火朝天的围填海和沿海开发不断蚕食着保护的成果。几乎与保护区建设同步发生的是,上世纪后50年内,中国损失了53%的温带滨海湿地、73%的红树林和80%的珊瑚礁;中国沿海的河口、海湾、滩涂湿地,因污染排放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重金属污染等,多数处于亚健康状态。保护在多数情况下输给了开发。
随着中国领导层近年来提出“生态文明”等顶层设计理念,并推行大部制改革和生态红线政策,中国近海环境保护是否有望重复中国在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等问题上的故事,迎来“拐点”?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关未来中国渔业捕捞、水产养殖和沿海开发的走向。
从无到有
中国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同步。1980年蛇岛建成第一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之后三年,中国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简称《海洋法》)通过,海洋保护区建设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1990年,负责制定和执行海洋保护相关法规的国家海洋局,设立了其管理的首批五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由国务院制定的专门管理海洋保护区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也于1995年应运而生。

中国主要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大多在《海洋法》通过后的20年间建立。例如位于渤海湾的辽宁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92年建立,1997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海洋哺乳类动物保护区。
2000年以后,国家海洋局开始将重心放在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上。相比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概念更宽泛。除了“海洋生态系统敏感脆弱和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它还可以用来保护历史文化遗迹,甚至那些适合进行未来产业发展的预留区域。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湿地中心副主任廖国祥表示,海洋特别保护区其实是在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
2002年,福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方政府批准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由海洋局制定的、专门管理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于2010年颁布。相比起需要国务院批准才能设立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设立只需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准,审批级别相对较低。截至2016年,中国已经有了近八十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包括各类海洋公园、重要的海岛和油气资源开发预留区域等。
在经历了近40年的建设,特别是近几年的积极发展后,中国近海形成了12.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网络,相当于英国国土面积的一半。2012-2017年五年期间,中国海洋保护区占中国管辖海域面积的比例,就从1.2%提升到了4.1%。中国似乎迎来了海洋保护区建设的高潮。
不过相比世界各国管辖海域内平均14.4%的保护率,这个数据还很低;比起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达成的在2020年将各国10%管辖海域纳入保护的目标,也还有不小距离。
参差的保护效果
和全球其他国家的海洋保护区一样,虽然名为“保护区”,但不同的海洋保护区保护力度不同。有研究认为,要取得理想的保护效果,一个海洋保护区需做到禁渔、监管得力、建立时间长(大于10年)、面积足够大(大于100平方公里)以及有天然屏障阻隔人类活动。至少要有其中三个要素,才能实现有效保护。
如果按照上述标准,中国只有早期建立的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符合要求。几乎近十年才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海洋特别保护区,因为在设计中就或多或少允许一定程度的开发,其保护效果要打上折扣。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处代表张琰说,中国的海洋特别保护区试图平衡开发和保护功能,通常只能对应到IUCN第五类保护区——同时满足保护和游憩需要的景观保护区,距离高等级的保护区尚有距离。而海洋特别保护区中的“潜在矿产、油气开发区”的保护等级甚至更低。
当然,保护效果打折,也与中国保护区多部门管理力量分散、以及监督力量不足有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为由国务院统一批复,且多数有专门管理机构,管理层级较高,保护效果相对较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则全部由海洋局批准管理。除此之外,各种层级更低的保护区则由许多部门批准和监管,如农业部门管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林业部门管理的“湿地保护区”,以及环保部门参与管理的多种类型保护区等。
这种分割管理模式,不仅导致单个部门想要申请大型保护区并不容易,也使得部门间争相划定保护区,同一区域可能有多部门管理。如江苏盐城珍禽(丹顶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归环保部门管理;与这个保护区重叠的还有一个国家级麋鹿保护区,归林业部门管理。一些海洋特别保护区,也同时挂了风景名胜区的牌子,同时接受海洋局和旅游管理部门的监管以及资金支持。
“中国海洋保护区管理是比较乱的,在(2018年3月大部制)改革之前,涉及海洋保护区管理的部委非常多,包括国家海洋局、国家林业局、农业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廖国祥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报告认为,由于海域环境的使用由数量繁多的社会群体分享,最理想的情况是由一个政府部门管理一个保护区内所有的活动,并在保护区的设计阶段充分纳入多个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保护和开发并进
部门分割还不是中国海洋保护区面临的最大威胁。中国过去四十年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对中国近海环境保护的努力带来了最直接的冲击。
上个世纪,中国沿海共有过三轮的大规模填海,包括建国初期的围海场建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围海造田,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围海养殖潮。
进入新世纪后,沿海经济发展加速,大型沿海港口、临海工业园、沿海经济带开发纷纷向海要地,掀起了第四轮围填海潮。
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也激发了中国近海渔业的大发展,从1995年开始近海捕捞总量就在每年1000万吨以上,大大超过渔业专家建议800-900万吨的最大可捕捞量。
保护和开发,就像在赛跑。原本应当受到保护的区域被开发的情况屡见不鲜。仅2005—2012 年间,就有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9 个沿海、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被调减,调减面积达5756.77 平方公里。
2018年7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试图给激进的沿海开发和围填海踩刹车。
国家海洋二局研究员曾江宁在文章中提到:“自然岸线的大量消退、滩涂成块连片的快速消失和浅海高强度的渔业捕捞活动造成近海生物多样性的下降。”
海洋生态红线
从2012年起,在国务院监督之下,渤海湾三省一市(辽宁、山东、河北、天津)开始了“海洋生态红线”的试点。海洋保护区建设似乎出现了转机。
在试点基础上,2016年,国家海洋局出台了《关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标志着全国海洋生态红线划定工作全面启动。
中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提出“生态保护红线”概念,但直到2017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责任主体,生态红线作为一项环境政策才慢慢展现出它的约束力。
全国生态红线制度给乱象纷呈的海洋开发带上了新的“紧箍咒”,其中一条红线就是海洋生态红线区面积占沿海各省(区、市)管理海域总面积的比例不低于30%。
这个目标给创造更大的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想象空间。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认为,海洋生态红线的设立是为了抢救性地保护一些生态系统。“一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他说,“等待建立保护区太慢了。”
红线区域分为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按照红线划定准则,所有的海洋自然保护区都属于禁止开发范围之内,而限制开发区域,主要是一些尚未纳入保护范围但有保护价值的区域,如重要渔业水域、滨海湿地,珍稀濒危动物集中分布区等。
配图:根据辽宁省政府办公厅2017年公布的海洋保护区和海洋生态红线地图制作。除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含特别保护海岛)之外,所有其它类型的区域都是生态红线制度下产生的禁止开发或限制开发类区域。
“如果把所有的红线保护区算进来,中国受保护的海域面积将大大增加。”廖国祥说。
虽然廖国祥和王亚民都看好海洋生态红线的保护作用,但到目前为止,海洋生态红线的划定尚无法律依据,“限制开发”这样的模糊规定恐怕也难以保障红线区域的保护效果和力度。
近海生态管理格局巨变?
2018年3月,中国公布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将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等下辖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统一归入自然资源部下新组建的国家林业草原局管理。
那就意味着,由多部门分散管理多年的各类海洋保护区,终于有望归入一家了。此前因为部门分割、陆海分治造成的海洋保护区管理问题,在中央政府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出现了改善的曙光。
但大部制改革只是开始。一些工作的落实还要等待各部委下属职能机构设置完全确定,而这些后续改革会影响到保护区的保护效果。
例如,在改革之前,环保部每年会对全国所有的自然保护区进行检察,并出具年度环境公报。现在自然保护区全部归入自然资源部管理。自然资源部是否还会延续环保部此前对保护区的环境监督手段,尚没有定论。
此外,各类海洋保护区快速增加带来的管理挑战,以及如何整合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管理法规,都是近期要面对的问题。
“一些类型的海洋保护区,如渔业保护区,已经(建设了)几十年了,积累了一些好的管理经验。(改革后)渔业部门会把所有的经验都交给一个原来以陆地保护为主的部门吗?”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海洋法专家薛桂芳表示。
但薛桂芳教授同时认为,改革过渡期虽会涉及到许多部门利益的调整和纠缠,但是中国加强海洋保护的趋势是明确的。
感谢跨境环保关注协会(CECA)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