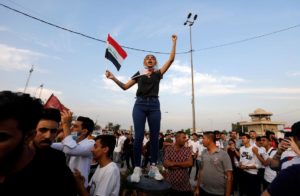六年前,深圳青年王鹏因售卖数只繁育的鹦鹉而被判刑五年,成为轰动一时的“深圳鹦鹉案”。该判决的法律依据认为人工繁育的鹦鹉属于《刑法》中“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所指的“珍贵、濒危”动物,受到各方质疑不合情理。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终于发布了最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试图解决“鹦鹉案”所凸显的司法实践问题。
这份20条的解释对涉及野生动物案件的定罪量刑做出指导,要求在公诉和审判实践中考虑涉案动物是否为人工繁育、物种的人工繁育现状、野外濒危程度等情节,区分情节轻重,拉大两者定罪量刑的差距。部分“轻微情节”将被免予起诉和处罚或是直接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份看起来更加“合情”的司法解释在受到部分法律界人士和动物养殖户欢迎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这种“从轻发落”是否会带来野保困境的担忧。
“不合情理”的判决
在“鹦鹉案”中,王鹏因拥有和售卖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一和二(等同于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鹦鹉而被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王鹏不服上诉,二审辩护人以人工繁育动物不应作为野生动物为由作无罪辩护。
2018年,二审法院承认出售人工繁殖动物社会危害性小于出售野生个体,但仍根据最高法2000年《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2000动物犯罪解释”),认为《刑法》所说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个体,因此减刑但不除罪,破例将刑期减至两年,低于法定最低刑——五年。
判决一出,大量舆论认为它机械地将人工繁育个体等同于野外种群,是违背公众一般认知的机械司法的典型。刑法学者罗翔在二审落槌后撰文表示这依然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因为当事人王鹏并不知道人工繁育动物在《刑法》上属于野生动物,因此“不知者不罪”。连《人民日报》都发文指出是普法的不足导致王鹏在不知中触犯法律,也让公众觉得判决不合情理。

一审宣判后媒体梳理发现,光是2015至2017年的21份判例中,就有32人因买卖鹦鹉被判触犯《刑法》,并被处以从缓刑到11年不等的刑期。在王鹏案之后,又出现了“江西鹦鹉案”、“昆明鹦鹉案”等类似的案件,同样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王鹏案二审辩护律师斯伟江和徐昕看到了此案的标志性。在2018年二审宣判后,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建议,要求对2000年动物犯罪解释进行审查,并获得了回复。复函中告知,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已启动了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司法解释制定工作,“拟明确规定对于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的要体现从宽的立场。”
4年后,这份司法解释问世。王鹏案和诸多类似案件的影子在其中浮现。在与此次司法解释配合发布的“答记者问”中,“两高”相关负责人强调对涉及野生动物案件的定罪量刑须“确保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它特别举了“江西鹦鹉案”中的费氏牡丹鹦鹉作为例子,称该物种虽被列入CITES附录二,但在中国养殖技术成熟,却因为“历史原因”普遍证件不全。他们提出对于此类案件,“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特别慎重,要重在通过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加以解决”。
这份新司法解释在4月9日生效。据报道,4月18日,山东禹城市王磊购买30只人工繁育赫尔曼陆龟(CITES附录二物种)案就被以法律发生变化为由撤诉,被认为是新司法解释被用于司法实践的第一起案例。
人工繁育:被网开一面的痼疾
对新司法解释的公众反应呈现出分化。一方面,是一些曾代理相关案件的律师和一些野生动物养殖户对此表示欢迎。有律师对媒体表示新司法解释将涉及人工繁育个体和野外个体的案件区分对待“是一种进步”,有养殖户说《解释》的出台令他们激动,“仿佛迎来了春天”,王鹏则告诉记者,《解释》的出台让他的“牺牲”有了意义。
与此同时,它却引发了保护工作者和一线执法者的担忧。担忧来自两方面:
第一,它提出以涉案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的货币价值高低来区分情节严重程度,而不再如过去那样以涉案动物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它设置了根据不同情形最低一万或两万元的入刑起点,这意味着涉及“低价值”动物的案件,将不会再出现“一只入刑”的情况。在两万元的入刑起点之上,它还设置了两万到二十万元(情节较轻)、二十万至两百万元,以及两百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三个等级,并设定了减刑情节。如果涉案动物价值超过两万元但低于20万,根据本次释法,只要行为人具有未造成动物死亡、全部退赃退赔、有悔罪表现等从轻情节,依然可以不被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甚至不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国家林业局2017年《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4只小熊猫、19只猕猴、39条眼镜蛇的评估价值都不满20万,以上动物都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此,有野保志愿者撰文表示担心许多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实际都会“降档量刑”。
第二,新司法解释宣布废除“2000年动物犯罪解释”,区别对待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与来自野外的野生动物的案件,提出涉案动物被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和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被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案件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如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则从宽处理。
很多野外猎捕的动物恰恰是打着人工繁育的幌子进入市场的。韦凯雯,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韦凯雯(Amanda Whitfort)告诉中外对话:“本次释法区分涉及人工繁育和野外动物案件的基础是认为买卖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不会影响野外种群及其生态系统。但是,很多野外猎捕的动物恰恰是打着人工繁育的幌子进入市场的。”她认为,不再把对据称是人工繁育濒危物种的贸易、持有和使用作为刑事案件,可能会加剧世界范围的盗猎和走私问题,鼓励非法贩卖者继续犯法。
一位从业超过三十年的森林公安民警告诉告诉中外对话,本次司法解释将证明涉案动物是人工繁育还是野外猎捕的举证责任重心转移到了公安和检察机关。在过去,是犯罪嫌疑人需要出示涉案动物的人工繁育许可证和专用标识来证明动物为人工繁育,从而为自己脱罪,而今后,公安和检察机关必须证明动物来自野外猎捕才能定罪。他表示,这给基层野生动物执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目前没有任何鉴定技术可以准确区分野外和人工繁育个体。他举例说:“比如我看到有人提了一只被打死的白鹇下山,上去问他白鹇是哪里来的。对方说是自己养的,飞到山上去了,他把它打死拿下来,我们就基本拿他没办法。就算有目击者证明亲眼看到他打野生白鹇,或有人证明他家从来没有养过白鹇,也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如果是跨省大批量非法贩运野生动物,要追究刑事责任就更难了。”他预计,未来大量案件将因为公安机关无法证明涉案动物是野外个体而不了了之。“办案者可能会畏惧接手这样的案子。”他补充道。
虽然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相关案件可能从此被移送给林草、市场监督、渔政部门,成为行政执法的对象,即所谓“刑行衔接”。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繁育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物种,应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和专用标识,没有这两者,依然应该予以行政处罚。但是这位民警表示,现存的大量证照齐全的养殖场可以用来“洗白”非法猎捕的野外个体,让行政执法也举步维艰。
比如黄麂是一种极为敏感的动物,在人工环境下很难繁育后代。他调查过省内所有的黄麂养殖场,发现没有一家养殖成功。“你办一个表面上合法的养殖场,然后通过不负责任的管理机构给你发放专用标识,你就坐地收购猎捕来的黄麂,不断收不断卖。”这些养殖场事实上的功能是“洗白”来自盗猎盗捕的野外个体。他又以蛇为例,他曾发现养蛇场在繁殖季节收购野生怀卵母蛇,用繁殖箱孵化小蛇作为“人工繁殖个体”出售的现象非常普遍。“当你看到养蛇场大量存在,你就不寒而栗。”
那么,未来究竟涉及哪些动物的人工繁育个体的案件将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其中一部分已经明确,那就是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动物,已公布的名录包括9种陆生动物和34种水生动物。但另一部分——“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新司法解释却没有提供认定依据。有人担心未来“作为宠物买卖、运输”可能为包括食用在内的各种目的提供借口。
逐步扩大的“人工繁育”边界
而关于何谓“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目前并无正式文件界定。2003年国家林业局曾发布《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此后最高法曾宣布名单上的动物不属于《刑法》规定的犯罪对象。但这份名单已于2012年废止,尽管此后它依然被部分司法机关用于审判实践,作为减轻处罚或做无罪判决的依据。
国家林草局办公室执法监督处处长汶哲的一篇文章认为,新司法解释实施后,这个问题将成为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争议焦点,“面对即将到来的司法机关咨询、当事人诉求,林草部门需要研究‘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的物种认定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两高”释法将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除罪化”的同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也在扩大合法利用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边界。新司法解释生效后一个月,国家林草局就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专用标识管理征求意见。这是林草部门首次试图为陆生野生动物正式建立专用标识制度。与其一同公布的第一批标识使用范围包括19种人工繁育的作为宠物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体,包括费氏牡丹鹦鹉、绿颊锥尾鹦鹉等12种鸟类,以及苏卡达陆龟等7种爬行类,外加药品、保健品、标本、皮张制品,生物制剂和工艺品等“野生动物制品”。

这个使用范围在2017年国家林业局“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和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该目录包含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允许人工繁育利用的陆生野生动物的范围,或将成为未来国家林草局发布“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物种的一种机制。
在上述19种被允许作为宠物繁育贩卖的动物中,有15种在中国没有自然分布,是根据CITES附录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仅4种在中国有自然分布。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环境调查署(EIA)发现其中非洲灰鹦鹉、辐纹陆龟被列入CITES附录一,并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分别评估为濒危和极度濒危,折衷鹦鹉的亚种桑巴岛折衷鹦鹉也已被评为濒危物种。该机构在提交给国家林草局的意见反馈中写道:“如果这些物种的商业利用和贸易在中国被合法化,中国市场对野外捕获的种源的巨大需求将威胁野外种群。”
国内保护工作者则质疑此举会导致外来物种逃逸进入野外,影响本土种群。而为数众多允许人工繁育和流通的物种,也让执法人员难以辨认,增加监管难度。
“刑行衔接”任重道远
“两高”在前述“答记者问”中表示将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双向衔接机制,防止案件处理在新司法解释之后“一宽了之”。但两者的衔接任重道远。“我们都认为这次市场监管局、林草局的行政监管责任更强了,想要胜任还需要大量的努力。”上述森林民警表示这是同行的普遍看法。“短时间内建立强大的行政执法力量来填补森林公安执法力量的空档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加强县一级野保部门的正规化执法能力,是当前非常紧迫的工作。”他补充道。
国家林草局汶哲的文章认为,新司法解释由于设定了多项不予起诉、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节,因此将“客观上增加行政执法工作量”,因此文章提出“林草部门需要切实加强执法力量配备,确保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力度不减。”
野生动物保护力量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为刑事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出具认定意见难度很大。
这篇文章还提到,本次司法解释第十七条提出,司法机关可将涉案动物的种属类别、是否系人工繁育,以及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专门性问题委托给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文章认为“这给主管部门提出了新课题”,它写道:“基层林草部门普遍反映,野生动物保护力量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为刑事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出具认定意见难度很大。”这势必制约主管部门未来开展行政执法的效力。
本次司法解释的初衷是提供司法救济,包括对那些盗猎和走私少量野生动物的“普通人”,但动物却不会陈述自己受到的伤害。香港大学的韦凯雯表示,法官和检察官充分了解野生动物犯罪对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在世界各地,这种信息都不为法官和检察官充分了解,以至于很多案件被不恰当地从轻发落。因此,她的团队发起了“物种受害者陈述计划”,与科学家合作,整理野生动物盗猎与走私的生态影响,提交给法庭作为审判依据。在香港法官和检察官使用了这种受害者陈述之后,野生动物走私案件的定罪量刑已经显著提升。
一位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中国专家告诉中外对话,如果是为了解决轻微情节的司法救济问题,那就应当追究那些把野生动物买卖炒作起来的人的责任,而不是把人工繁育整体除罪化。她认为这是本次司法解释“失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