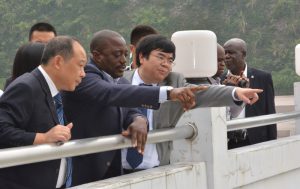本文获得最佳环境报道奖的“最佳绿色经济报道”奖。
颁奖词:闫笑炜做出了突破:他深入多个垃圾发电厂调查,揭示了这个产业灰色的利益链条和鱼龙混杂的潜规则。
垃圾发电,被认为是城市废弃物“变废为宝”的最优循环经济解决方案。但这个看似美好繁荣的“循环经济”外衣下面,充满着各种假象与骗局。
从东莞出发,沿环城路西行约30分钟,即可经过小镇横沥,继续行驶约5公里,则可看到一座封闭的厂区。在微风中,黄蓝双色的司旗伴随国旗猎猎作响;厂区门口,烟尘、二氧化硫等排放信息滚动播放,厂区的锅炉烟筒冒着烟气,来往的垃圾车卸料时发出的轰鸣,打破厂区特有的宁静。
这里就是珠三角最大垃圾发电项目——横沥垃圾焚烧发电厂所在地。它隶属于粤丰集团的东莞市科伟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今年9月,这里刚刚完成循环流化床升级水冷振动炉排炉的改造。
上世纪80年代末,从深圳落成第一家垃圾发电厂开始,国内垃圾发电的淘金序幕被缓缓打开。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垃圾和填埋场的逐渐饱和,垃圾发电渐渐被认为是最具前景的垃圾处理方式。从那时起,垃圾似乎多了一个身份——一方面它是城市里急需处理的固体废弃物;另一方面,它是循环经济,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能以最经济、直接的方式,源源不断的提供电力。
但似乎任何一个产业都摆脱不了的命运,经历了约十年的黄金时期,围绕垃圾发电的争议也愈演愈烈,披着“循环经济”外衣的垃圾堆场,一方面被质疑恶意套取国家垃圾处理补贴资金,另一方面,也不断因环保问题被屡次推向舆论风口浪尖。
11月下旬,《能源》记者赶赴国内多处垃圾发电项目调查得知,真实的垃圾发电产业,正如位于横沥镇的垃圾发电厂一般,美好的外表下,掩盖了灰色的利益链条和鱼龙混杂的潜规则。
公关潜规则
11月上旬,张铭源(化名)的一个重要行程是前往西安参加位于国际展览中心的环境博览会,向展台参观者介绍公司的业绩和技术实力。
张铭源是一家垃圾发电公司的董事长,除了参加展会外,他来到西安的另一个目的,是参加即将开始的垃圾发电项目招标,角逐当地垃圾发电入场资格。
不久前,西安市政府释放出兴建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根据陕西环保集团的数据统计,西安日平均产生生活垃圾7000-8000吨,夏季甚至可以达到9000吨。但大多数生活垃圾均以填埋处理,由于填埋场的日益饱和,西安市政府打算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替代传统填埋场。如果以平均处理量2000吨的填埋场来看,西安市至少需要5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才能满足生活垃圾处理需要。
近些年,由于环保行业的由冷至热,不断增长的垃圾量和填埋场的日趋饱和,垃圾焚烧发电的境遇也随即改变。相对于动辄上亿,蜂拥而上的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垃圾发电具有更小的经济规模;与传统的生物质发电相比,垃圾发电原料收集更稳定,而且技术实现了市场化。在高额的垃圾补贴的诱惑下,从业者只要保障原料充足,就掌控了稳定的收益,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们沉迷于垃圾处理补贴和售电带来的暴利机遇。
张铭源旗下的公司,早在上世纪末建成了东莞第一座垃圾发电厂,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他算是垃圾发电行业的元老人物,不过,和当初的踌躇满志相比,他们似乎对成功中标西安项目并未抱太大希望。
“我已经多年没有从事垃圾发电新项目的投资了,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太大竞争优势。”张铭源向《能源》记者坦言。
近些年,由于地方保护,他手中拿到项目越来越少,但另一方面,每一次角逐垃圾发电,对他来说都意味着一次巨额支出。
不久前,他曾参加湖南永州日处理1400吨项目竞标的垃圾发电项目。从项目前期调研到参与竞标,各项花费加起来有800万元之多,除了制作文件、项目调研外,很大一部分,还是用来打通各层政府关系。
“记得当时,当地环卫局领导家有喜事,我们给他们随礼,现在查的严,随礼都不敢署名,关系不好,甚至都不敢收你的随礼。而且,随完分子马上得走,根本不能留下吃饭。”张铭源给《能源》记者爆料。
即使如此,张铭源仍然未能中标永州垃圾发电项目,该项目最终被一家国企背景的竞争者所获得。
此外,这几年,张铭源感觉投标中的‘绑架’氛围也越来越浓。由于看到了垃圾发电的盈利前景,许多拥有政府关系的商人也纷纷涉足垃圾发电。他们大多没有业绩,不具备投标资质。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曾表示:“决定是否中标有三个因素:关系、价格和技术。现在,技术已经拉不开距离,关系和价格是最重要的。”
一般来说,投标垃圾发电都会有一个准入门槛,投标企业必须有运营500吨/日处理量的垃圾发电厂才能投标,这表面对竞标公司起到规范作用,但招标文件中,却隐含了不少猫腻。
“假设符合资质的企业有6家,没有资质的企业也想参与投标,政府在招标的时候,会注明‘允许联合投标’,然后暗中要求具备资质的企业带着没有资质的企业联合投标,中标后,联合投标企业会享有‘干股’坐享收益。这些项目,可以对外说是自己的业绩,其实不少企业的业绩就是这么来的,有了业绩以后,可以到其它地方光明正大跑马圈地了。这其中,有不少公司都是政府亲戚朋友介绍过来的。”张铭源告诉《能源》记者。
由于垃圾发电的业主一般是政府环卫部门,垃圾发电招标结果往往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尽管形式上中标公司由评标委员会决定,评标委员主要成员由招标公司从专家库中抽选。但在现实操作中,评标委员会对结果影响有限。其一在于招标公司对专家具有选择权,“不合作”专家下一次则不会被邀请。其二在于专家需根据政府制定的招标文件打分。一位以循环流化床为主要技术的垃圾发电从业者对《能源》记者表示:“有时候,政府关系的企业采用水冷振动炉排炉,那么招标文件中,干脆就把以流化床为主的一些企业排除在外”。这样环卫部门利用手中的自主选择权,确立招标细则,进而按照自己意志来选择BOT公司。
对于此次西安招标状况,张铭源摇摇头,不愿多谈,但他表示:“参与投标一共有20家单位,要和当地企业竞争还是很难。”
这些潜规则,若不是张铭源爆料,目前仅在行业内部流传。然而,即便一些企业千辛万苦最终获得路条与核准批文后,垃圾是否真如一些行业人士所期望的,能够成为一座待挖掘的宝藏?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盈利谜团
贵州兴义市垃圾发电厂内,白底蓝条的专用密闭垃圾清运车载着垃圾,顺着栈桥进入全密闭且微负压的卸车大厅,20吨垃圾“哗哗”倒入垃圾池。
据了解,该项目由鸿大环保电力公司设计运营,生产的电力最终并入兴义电网,炉渣可用于制作建筑材料。一期项目,其垃圾处理量被设计为700吨/日,并网后的项目每年生产电能约1.4亿千瓦时。
据透露,这一满载设计700吨的垃圾发电厂,当时日处理量只有500吨左右。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曾为《能源》记者做过一笔测算:“垃圾发电,收入主要来源于上网电价和垃圾处理补贴。而承担的成本,主要包含设备购买维护、人员等,这些基本是固定成本。但其收益则与垃圾处理量息息相关。一般来说,日处理600吨垃圾,其补贴与上网电价收益才能达到垃圾发电收支平衡点。但由于不同地区垃圾热值,燃烧条件以及所采取的技术路线不同,部分专家认为这个收支平衡点应当在1000吨/日上下。从数据来看,鸿大环保日处理量在500吨,处在盈利平衡点之下。”
另一方面,决定垃圾发电项目盈利能力和项目所在地有很大的关系。粤丰集团科伟环保电力总工程师李德明告诉《能源》记者:“早期的垃圾发电项目基本集中在发达地区,一般来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垃圾资源充足,垃圾热值较高,加上政府资金充裕,垃圾发电厂满负荷运行,盈利状况都很好。例如,粤丰集团旗下东莞日处理2000吨项目,改造投资6个亿左右,但8年即可收回成本。”
在沿海地区之外,项目盈利情况有所不同。锦江集团副总经理任光惠曾向外界表示:“山东菏泽锦江垃圾电厂为例,因为发电规划不周,电厂出产运转率仅为35%;垃圾发电本钱为0.397元/度,而其施行的暂时电价仅为0.285元/度;加上政府许诺垃圾燃焚的补贴迟迟不能到位(每燃烧1吨垃圾,索取10元补助),招致其临时亏损。”此外,业内人士透露,由于一些项目盈利能力不佳,锦江集团最近在考虑将其出售。
早期以轻纺业起家的锦江集团,由于电力供应不足,并购了嘉兴一带的自备电厂。当时,自备电厂成本低廉,进行流化床改造后,这些自备电厂可以以垃圾取代燃煤作为发电原料。这无意中的收购,为锦江集团创造了巨额财富。然而,在锦江集团走向内地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项目所在地不同,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有所差异,各地上网电价和垃圾垃圾处理费不同,以及政府的补贴是否到位都决定这一个项目的盈利状况。
锦江集团并非个例,国内另一垃圾处理龙头企业光大集团,其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项目有着良好的盈利能力,但走向内地,也面临着垃圾处理量不足,上网补贴等困境。
“由于垃圾处理量决定着项目收益,因此政府对垃圾的规划很关键。”张铭源表示。
例如,昆明的垃圾发电规划饱受业内人士诟病。作为最早招标垃圾发电的内地省会城市之一,昆明早在2008年即开始垃圾发电的项目招标。根据规划,2020年全市四城区的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将达到7000吨/日,昆明市计划兴建5座垃圾发电厂,最终中标的包括当地企业云南环能电力、锦江集团、中德环保等。
“当初我们是根据政府的规划制定的可研报告,以为垃圾收集完全没问题,结果项目投运才发现实际垃圾产量远远没达到这个数字。由于项目多垃圾少,一些设计指标为1000吨/日发电厂日处理量只有500吨左右,处在盈亏平衡线之下。”一位当地垃圾发电从业者告诉《能源》记者。
虽然不少二三线城市也开始考虑以焚烧发电的形式处理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但多名业内人士均认为适合做垃圾发电项目的地方越来越少。
相比之下,企业的策略截然不同。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光大集团作为国企,有发改委资金支持,再加上上市公司的背景,完善的产业链,其战略也是将垃圾发电作为产业来做,并不会考虑某个项目盈利问题,但以盈利为目的锦江集团,会考虑出手一些盈利能力较差的电厂,而业务中心会逐步转向其氧化铝产业。”
沦为圈钱的工具
几家欢喜几家愁。一些企业谨慎前行的同时,却有一些企业快马加鞭的跑马圈地,在《能源》记者调查了近些年落成的垃圾发电项目后发现,跑马圈地的企业以上市公司居多。
一般来说,垃圾补贴决定着一个垃圾发电厂的收支平衡,补贴高,投资回报周期短。但有些企业甚至以飞蛾扑火之势,不惜以极低的垃圾处理补贴竞标。今年8月,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26.8元/吨的垃圾处理补贴费中标安徽省蚌埠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刷新了内地BOT建设运行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垃圾补贴费最低记录。而不到两个月后,天津泰达以26.5元/吨再次中标江苏高邮垃圾发电项目,将记录再次刷新。
这种现象从本世纪初就初露端倪,2001年,国内第一个采用BOT建设运行的山东菏泽生活垃圾焚烧电厂,当时定的垃圾处理费是8元/吨,其后还有一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处理费定为20元/吨,30元/吨以及40元/吨。到现在,价格战已成常态,在实际的招投标中,政府指导价只是一纸空文,并无人执行。“正常中标价能达到指导价50%就不错了,极端情况下中标价甚至仅为指导价一成。”张铭源告诉记者。
相比非上市公司,这些企业资金链充裕。但跑马圈地的背后,企业诉求鱼龙混杂。
据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爆料:“不久前,国内一个国内知名国有企业,刚刚成立垃圾发电事业部,他们联系到我说有没有垃圾发电项目可以卖,由于急需业绩,当时要的很急,说哪怕年处理量400吨的项目,不盈利也都买了。对于国企来说,买了就有业绩。对于拿到项目的企业来说,这又是一笔暴利。”正是看中了这点,不少企业在获得项目后,做起了“二道贩子”。
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垃圾发电,是很好的公众热衷炒作概念。一些选择错误技术路线的投资方,通过手握25年或30年的特许经营协议,可以轻而易举地卖掉项目或者推倒重来,改建机械炉排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一过程投资方不仅没有损失,还可以把损失转嫁给政府或国有企业,由于政府过度保护投资者利益,往往投资方有恃无恐。此外,社会诚信缺失,助长投机行为。资本市场上,只要能够讲故事,股价就得到追捧。”
张铭源告诉记者:“近些年,企业也越来越聪明了,不少企业甚至学会了‘倒逼’政府涨价,一些企业把项目拿到手后,项目盈利状况较差,烟气排放也不达标。后来通过媒体曝光,使政府面临压力,最后政府出资改造烟气处理设备,并把生活垃圾处理补贴费一次性提高到120元/吨。”
但倒卖项目,只是其一,此外,也有不少上市公司靠着充足的资金链条,中标后,以“邻避效应”为由,搁置3年不建设。
“现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你中标后投不投运的问题。只要运营良好,包括尾气处理,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兴建一个垃圾发电项目,对于周边百姓来说,能带来非常多的隐形收入,譬如环境补偿,征地补偿等等,但如果经济补偿不到位,老百姓会抗议,形成所谓的‘邻避效应’。”以为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 《能源》 记者表示。
邻避效应,对政府来说是巨大的压力,但企业却获得了正当理由搁置项目。一般来说,企业只要拿到路条,就可以申请补贴,补贴一旦申请下来,就可以申请银行贷款,但许多企业拿到贷款以后,转而做别的项目。“昆明一共中标了4家公司,其中某个德国上市公司到现在项目拖着都不建设,转而投向房地产项目去了。”某位业内人士爆料。
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政府对恶性竞争的宽容,是造成恶性竞争,跑马圈地的根源。在日益饱和的垃圾填埋场中,环保诉求已成为垃圾发电的更大推动力,也是决定一个项目能否顺利实施的首要因素。但环保诉求带动的产业,却屡屡因环保问题被推向风口浪尖,这又隐藏了什么秘密?
排放造假:普遍规律
11月19日,在东莞市科伟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现场总指挥陈峰的带领下,《能源》记者参观了这座新建的垃圾发电项目。与臭气熏天的垃圾填埋场相比, 这里的空气闻不到一丝异味,厂房内充斥着显眼的环保口号,墙壁上,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信息每隔5秒钟滚动刷新。临行时,陈峰特地在记者面前的喷泉处洗了洗手。陈峰告诉记者,这些景观用水,都是厂区循环处理,处理结果达到了实现了零排放。
2014年,环保部出台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不少垃圾发电厂开始着提标改造。这些改造确实立竿见影,在显示屏上的各项数据中,二噁英的指标达到了0.1ngTEQ/m3,这已是欧盟排放标准。
但结束参观时,已临近午饭时间,随行专家仍然建议记者选择远离垃圾发电厂的地域用餐。
“这些数据有水分。”一位从事垃圾发电20余年的业内人士向《能源》记者透露:“别说他们了,我做垃圾发电厂总经理的那几年,有些事我都干过。当然并不是说二噁英什么的处理不了,主要是它检测起来非常困难。”
由于生活垃圾组分十分复杂,即使同一垃圾发电厂,来自同一地区的垃圾,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其组分也有所差异。在雨季,其含水量较高,燃烧不够充分,排放物残渣可能较多,而旱季就有所不同,因此,根据垃圾组分测算排放几乎不可能实现。通常,环保部门检测二恶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活性炭吸附,由于二噁英的主要物质是固体颗粒物,活性炭具有较好的吸附能力,因此,使用了多少活性炭,成为了检测垃圾发电厂排放是否达标的唯一参照物。
“这里面就有很大猫腻了,比如,环保部门来检测前几天,我们再上活性炭,这样活性炭用量也不是很大,完全符合环保部门的标准。”这名人士告诉记者。
一些企业,甚至在厂区旁边修建环保部门的办公大楼,在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显示自己的环保。由于垃圾发电厂牵扯了太多利益在其中,环保部门有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光是二噁英检测中的猫腻,另一大难题——垃圾发电后的飞灰处理问题也渐渐浮现出来。
不久前,光大集团在江阴的1400吨/日垃圾发电项目因飞灰处理等难题遭遇投诉,体现了垃圾发电飞灰处理面临的囧境。
由于飞灰的成分以不可燃烧的重金属居多,在我国《危险废弃物名录》中,飞灰已赫然在列。从技术角度来看,目前,飞灰主要工艺流程是先通过袋式除尘法收集,再用水泥进行固化,最终填埋,但随着垃圾填埋场的逐渐饱和,这一方法也备受质疑。
据陈峰介绍:“飞灰处理难题主要在于技术和成本,我们也一直在探索,但是当前,我们的模式是将它外包给威立雅,主要是为了避免飞灰处理不当造成的社会效应,至于威立雅怎么处理,这是他们的事。”
披着“循环经济”外衣的垃圾堆场,一方面被质疑恶意套取国家垃圾处理补贴资金,另一方面,也不断因环保问题被屡次推向舆论封口浪尖。
原文刊登于新浪能源杂志,中外对话转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