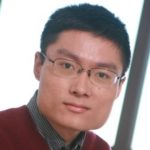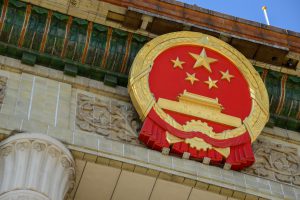“我们正处在一个环境保护和气候政策的十字路口,必须探索建立一个现代的环境治理体系”,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告诉中外对话。
3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是2019年11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环境治理领域“现代化”的第一份路线图。这份路线图以“党的领导”、“多方共治”、“市场导向”、“依法治理”为原则,共包含7个改革领域和28个要点。
2012年,在新一届政府走马上任伊始,马军曾撰文《中国未来十年新型环境治理体制刍议》,对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期待。过去几年,这位中国民间环保领域的领军者之一带领他的机构IPE深耕环境信息公开。他们开发的“蔚蓝地图”手机APP和每年进行的PITI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评估被认为是中国公众与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形成“良性互动”的样本。对于新提出的这份环境治理“现代化“路线图,他为中外对话进行了解读。
我们希望环境治理中更少一些“人治”,更多一些“法治”。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您怎么定位这份《意见》在中国环境法规政策体系中的位置?
马军(以下简称“马”):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由中办国办所发布的意见其政策指导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体现的是最高领导层的构想。这个构想逐步会在立法、政策、落实等各个方向上体现出来,把它作为一种原则去贯彻,应该讲定位还是非常高的。
中:如何理解“现代”这个提法?
马:“现代”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与最近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相互连接的。从内容上来看,《意见》体现了一些新的想法以及和全球环境治理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相吻合的一些方向。
环境领域在中国比较特别,参与其中的政府部门、立法机构和民间组织等比较早地提出了“公众参与”和“多元共治”等理念,并且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确立了一些良好的实践。《意见》比较好地总结和确认了这些实践,如环境信息公开、绿色金融等,但同时又面向未来地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意见》构建了7个主要体系,并落实为每一个环境治理利益方(政府、企业、公众)的主体责任,还特别提到了市场导向和公众参与,在理念上是先进的。
中:您在2012年的文章中提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应以公众的三大程序性权利(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司法救济权)为基础。此次的《意见》则详细确立了各利益方的责任。以“权利”为基础和以“责任”为基础,区别在哪里?
马:将近十年前,我们看到在环境领域中,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公众处于劣势。要真正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公众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当时,公众还缺乏参与环境治理途径。所以程序性的权利很重要,特别是知情权。公众不获得信息,就不会有后面的有效参与。
十年中,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公众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逐步向“良性互动”转化。公众运用手中的数据去参与环境治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环境信息不仅帮助公众做好自身防护,也使得他们能够参与环评等决策过程,监督污染行为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作为人权一部分的环境权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原点,也是构建环境治理法律体系的基础。201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就明确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意见》与《环境保护法》在脉络上是承接的。但《意见》更多地是在操作层面上构建实际的环境管理方案,是结果导向的,这时候它就更多地强调各方在推进落实中的责任。同时,《意见》中关于社会监督机制、公益诉讼等机制的内容,虽然没有点名“权利”两字,但已经隐含着对公众权利的确认。
中:我们注意到《意见》对企业信息公开规定得非常具体,但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着墨不多,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马:《意见》与其他的法规政策是相连接和延续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有相关的法规政策约定。根据我们的长期跟踪评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这些年取得长足进步。但企业的信息公开却有些原地踏步,远远不能适应环境治理需求。因此,《意见》更多强调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企业级的环境信息公开也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之一。公众很难去跟企业一家一家地博弈,来满足知情权。最终还是需要政府去落实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政府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政策制定、机制设计和最终落实方面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您认为《意见》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短板吗?
马:《意见》中的相关内容体现的还是现有法规的要求,没有直接去突破它们。例如对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出应公开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和执行的标准,但不要求公开排放量等信息。我们认为,环保部门应该引导企业更加完整地公开排放的信息,不仅排污量要公开,还应扩展到能耗、温室气体排放等信息。
《意见》中所强调的市场化环境治理方式,无论是排污权交易还是环境信用评价,没有企业级的排放数据公开,都是不完整的,在实践中操作起来也会不到位。
中:您强调了环境信息对市场化环境治理手段的基础性作用,《意见》中也专门提出建立环境治理“市场体系”,强调要引导资本参与环境治理、开展排污交易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为何要在当下强调“市场”?
马:市场化的环境治理方向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一个自然的结果。环境治理各利益方的深度互动促进了一些市场化治理机制的发展。例如,近期已经开始有国有银行机构试点应用IPE基于大数据研发的百万级企业环境信用动态评级系统,在贷款全流程监控企业的环境表现。绿色债券的发行也开始利用这些数据。
《意见》在此时强调市场化环境治理的时机也非常关键。过去五年,中国执行了最严格的环境法规,其中很大一部分重点放在落实政府领导责任,建立了追责、督察等制度,迫使各级政府部门下大力气治理环境污染。但近期受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为主的环境治理方式难以像过去几年那样维持其力度。一些地方希望能够“松绑”环境管理力度,而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的经济刺激措施也会是超大规模的。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环境保护和气候政策的“十字路口”(crossroad)。为了避免重新回到为经济增长而放松环境监管的老路上,我们必须探索建立一个现代的环境治理体系,去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社会监督的方式治理环境。因为市场化环境治理的经济影响是最小的。它本质上是构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优胜劣汰,遏制“黑色的GDP”,鼓励“绿色的GDP”。对于迫切地需要恢复经济的中国,市场化解决方案可能对平衡发展和保护发挥关键作用。但市场化的治理方式需要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否则也可能出现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
中:在强调市场的同时,《意见》也强调了“党的领导”。如何理解党组织深度参与环境治理的意义?
马:中国在各个管理层级上,党的职位都是实质上的“一把手”。现在要求“党政同责”,即党的负责人也对环境负有责任,而不仅仅是问责政府的负责人。在现实中,这会增强环保政策的落实力度。
但我们也看到,《意见》在提到“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强调了“依法治理”原则。这两者之间需要相互结合去看。我们希望环境治理中更少一些“人治”,更多一些“法治”。虽然“人治”有时速度更快,但容易走偏,形成一些过度的和“一刀切”的做法。现代环境治理要建立在法治(Rule of Law)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