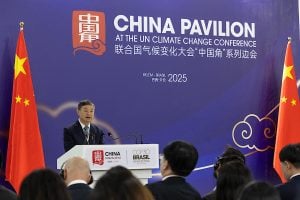这个夏天,“垃圾不够烧”意外成为中国的热点话题。离全国热议的上海强制垃圾分类仅仅过去了6年,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几年内就彻底走出了“垃圾围城”的困扰,从此可以在垃圾问题上高枕无忧了。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垃圾不够烧的本质,是垃圾焚烧产能过剩,是特定经济阶段的政策驱动与市场需求错配。背后的隐忧,今天也正在浮现。
焚烧曾是门好生意
本世纪初期,垃圾填埋场作为主流模式已经无地可扩,而且有渗沥液和甲烷等环境问题,产业政策急切地想要推广垃圾焚烧技术——焚烧厂不仅占地少,技术性高,而且垃圾可以处理彻底,在确保操作标准的情况下,垃圾焚烧环境遗留问题少。
当时,焚烧厂曾经是门好生意。尽管焚烧厂的“单位投资”成本高,至少40万元/吨,是填埋场(约10万元/吨)的至少4倍,但垃圾焚烧的处理费也比垃圾填埋的处理费高,后续运营也有保障。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公司合伙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转移财政压力,因此焚烧厂大多采取发债融资模式,企业可以更低成本获得资金,依赖政府补贴和垃圾处理费维系运营,现金流不错。
PPP模式为垃圾焚烧项目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18年垃圾焚烧处理量达到1.02亿吨,占全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总量的44.74%;到了202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06 亿吨和78.9%。可以说,中国用了不到10年,城市垃圾从填埋为主转向了焚烧为主。
全国焚烧厂数量从2010年的104座激增至当前的千座数量级,近10倍扩充仅仅用了15年时间,建成了接近全球三分之二的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
但以焚烧为主力的垃圾末端处置行业,正在面临三大挑战——收入来源的缩减、失控垃圾的漏洞、和“我们需要制造出更多垃圾”的灾难性幻象。
财政承压、补贴退坡
早前,除了垃圾处理费和一些零散收入,中国 垃圾焚烧厂的收入还来自于三部分:政府的补贴,垃圾发电的收入,还有可以开发自愿减排量(CCER)在碳市场上获取收益。但这三种收入来源都面临挑战。
2019年,财政部在对人大代表建议补贴的回复中明确表示,将逐步减少新增项目纳入补贴范围的比例,引导通过垃圾处理费等市场化方式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予以支持。
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策导向、财政压力、监管标准提高等等。
垃圾焚烧在中国被归类为生物质发电。2020年后并网的项目,补贴开始实行央地分担机制,东部地区项目的中央支持比例仅为20%,大头落在地方财政。《2021年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工作方案》明确中央补贴逐年退出。2023年起新投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这样垃圾焚烧补贴主要落在了地方财政肩上。另外,补贴核减有时被作为行政监管的约束措施。生态环境部2020年出台政策,对监测数据超标、设备不正常运行的项目实施补贴核减,且3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而地方财政近年来的压力显然易见,环保补贴作为非刚性支出常被压缩,出现补贴拖欠的地方更多。2025年3月,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举例:2024年10月,某企业三个生物质发电项目累计拖欠补贴超过4亿元,账龄长达4—5年。日处理量不足500吨的小型焚烧厂,所在区域财政实力更弱,更易遇到付款延迟的情况。
仅2024年上半年,环保行业上市公司的应收款高达349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14%。2025年,某家大型企业召开“应收账款回收经验交流会”,足见这个问题已成行业系统性挑战。
CCER的收入也归零了。据招商策略研究估算,2012-2017年期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通过出售CCER,每处理一吨垃圾可增收7.6元,每年可贡献3%-7%的收入弹性。德中环保咨询测算认为,头部企业通过自愿碳减排可以增厚收益8-10%。不过,2024年,CCER重启之后,垃圾焚烧处置由于方法学减排量小,而且有环境污染争议等原因,不再出现在 CCER 的适用项目类型中。卖碳的路一时半会走不通了。
什么是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CCER 是由中国政府认证的碳信用额,用于记录减少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例如可再生能源发电或植树造林。每一个信用额对应减少一吨二氧化碳,可在国家碳市场上进行交易,用以帮助企业履行减排义务。
CCER 机制最初于 2012 年启动,但因交易量低和数据质量问题于 2017 年暂停,并于 2024 年 1 月重新启动。
电力方面,以往垃圾焚烧电力有标杆电价和补贴撑着,每吨垃圾折算上网电量的280千瓦时部分执行每度电0.65元的全国统一标杆电价,超出部分按当地燃煤机组标杆电价执行,一般是每度0.25-0.4元。在新的机制下,电力的环境效益主要以绿色电力证书来承载。而绿色电力证书当前还在供需适配的过程中,2024年由于绿证核发数量激增,需求并没有跟上,因此大部分时间里每度电价格只有几分钱。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垃圾焚烧行业的运营压力相较十年前显著加大。截至2024年6月,全国焚烧能力达107万吨/日,超“十四五”目标33.75%,但行业平均负荷率不足60%,40%产能处于闲置状态,企业利润率下降。
视野之外的失控垃圾
垃圾焚烧行业的产能存在地理和城乡失衡。
胡焕庸线(即“黑河—腾冲线”,是中国人口密度、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格局的分界线。线东面积不到中国国土面积一半,但是分布绝大部分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以东地区,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焚烧厂,而西部及东北部分地区建制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于30%,远低于“十三五”相关规划提出的70%目标要求。
由于乡镇垃圾相对分散,收运成本高于城市,焚烧厂投资纷纷争抢城市、绕着农村走。很多偏远村庄仍然露天堆放垃圾、或以简易方式自行焚烧处置,环境隐患较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城市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海云2024年撰文称,人口密度小于100人/平方千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10个省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垃圾收运难度较大。10个省区总人口约3 亿人,目前已经建成和在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能力可服务人口约 2.1 亿人,还有近1亿人没有覆盖。这样,一面是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垃圾“不够烧”,一面是人口稀疏的地方焚烧厂不够。
另一个重要但易被忽略的现实是——关于垃圾规模的统计口径,只能覆盖被清运的垃圾量,但到底有多少失控垃圾被丢弃到人们视野之外,是无从统计的。乡镇农村地区因更靠近地表径流,农村垃圾露天堆放的渗沥液和塑料碎片更易进入水体,并进一步在自然环境中迁移,可能成为微塑料与有害污染物的直接来源。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2021年实证研究显示,北京怀河城市段沉积物中微塑料丰度低于被测河段平均水平,也就是低于河流的农村段。该河流微塑料主要来源于周边村庄的生活垃圾破碎风化及农业活动(如农膜残留),而城市段因污水处理厂截留部分污染物,沉积物丰度相对较低。中山大学同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珠江口枯水期微塑料平均丰度在雨季大幅上升,主要原因就是农村垃圾冲刷。
通过《“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中列明的工作重点可清晰地看出:农村塑料污染的关键,是农膜残留、塑料垃圾直接填埋和露天堆放。
削足适履的危险苗头
随着丰富的商品消费快速遍及农村地区,那些沦陷在收运体系和统计口径之外的失控垃圾,增长态势可想而知。
同时,“垃圾已不成问题”的高枕无忧心态,在客观上使减废更加困难。2016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超过2亿吨, 2024 年增至2.62亿吨。7年时间,增幅超过30%。人们越觉得垃圾处理不是问题、心理上越是认为有兜底方案,就越是不在意扔垃圾、行为上就越来越没有减废意识,垃圾也就增长越快。
《湖北日报》有评论认为:“‘中国垃圾不够烧了‘的论调,其实是偷换概念,把焚烧厂产能过剩的问题混淆为垃圾资源短缺。”笔者也深以为然。国内人均垃圾产生量并未提升,仍明显低于国际发达水平。如果为了填满焚烧厂的炉膛,在制造垃圾这件事上也要向更浪费的所谓“高水平”看齐、刻意鼓励更多废弃、更多一次性消费的行为方式,无疑是削足适履。
事实上,如果湿垃圾进入无害化处置的比例显著提高,如果更多的废弃物得到回收而不是进入末端处置,那恰恰是垃圾分类的突出成效。垃圾末端处置的原则,按照优先级排序是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减量是第一位的。应该做出调整的,是末端处置的产能供给和布局,而不是刻意制造出更多的垃圾来“喂养”焚烧炉。
归结起来,中国的垃圾问题不能简单靠““一烧了事“化解。3月,行业龙头光大环境发布2024年全年业绩报告称,随着垃圾量缺口、环保产业供需错配等问题的出现,公司需要从toG(政府)向toC(个人用户)和toB(企业)转变,使客户群体更加多元。
一个时代已成历史,垃圾焚烧行业需要重新定位、梳理固废无害化处置及其协同、供电、回收热能等等业务需求的空间并协调供给,也需要在收运格局的优化中扮演关键角色,管住”失控垃圾“,才能走出行业性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