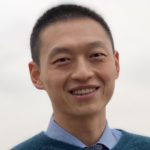2022年7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161票赞成,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宣布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一项普遍人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一“历史性”决议将“有助于各国加速履行有关环境和人权的义务及承诺”。
这项决议的先声出现在半个世纪前。1972年,人类历史上首次聚焦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达成了一份宣言,宣布享有能让人过上有尊严和安康生活的优质环境是一项基本人权。时隔50年,刚刚通过的联合国决议终于让这项权利获得了普遍认可。同时,该决议为气候相关条约的缔结、更多成员国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以及推进更具变革性的气候运动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各国气候变化诉讼层出不穷的当下,环境权决议可能成为推动气候变化诉讼实现人权转向的重要力量。
气候诉讼的“权利转向”
早在本次联合国大会承认健康环境权是普遍人权之前,试图以人权作为依据推动气候变化政策的行动已持续进行了多年。
2006年,居住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申诉书,指责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破坏了因纽特人的居住环境和文化等,要求美国负责。不过,该委员会以证据不足以确定损害的存在为由,拒绝对这一请愿进行裁决。2009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名为《关于气候变化与人权的关系问题的报告》,确认气候变化危害到了生命权、获取适足食物的权利、水权、健康权、住房权、自决权。2016年正式缔结的《巴黎协定》在序言中加入了关于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的表达:
“(各缔约方)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缔约方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应当尊重、促进和考虑到它们各自对人权、健康权、土著人民权利、当地社区权利、移徙者权利、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弱势人权利、发展权,以及性别平等、妇女赋权和代际公平等的义务。”
在此背景下,以保障人权作为诉请的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大量出现,学界称之为气候诉讼的“权利转向”(rights-turn)。
以人权为基础的诉讼中,原告的诉求并不限于具体个人或群体的权利遭受侵犯,而是尽可能多地列举受侵害的主体和权利。主张青少年、甚至未来世代的权利受到侵犯的尝试越来越多,因为显而易见,相较当代人,他们将承受更多气候灾难的后果。最早采取人权进路的气候诉讼为“Leghari诉巴基斯坦案”(Ashgar Leghari v. Federation of Pakistan),一位巴基斯坦年轻农民主张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充分,侵犯了他享有的基本生命权和尊严权。最有名的案件则是2019年底作出终审判决的“Urgenda案”(Urgenda v. 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原告主张荷兰政府因气候变化应对不力而未尽《荷兰民法典》中规定的注意义务,侵犯了《欧洲人权公约》所保护的生命权及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
上述两起案件的原告都赢得了胜诉,但并非所有把气候变化与人权相连的尝试都能成功。例如,挪威最高法院认为政府发放北极采油许可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宪法权利的侵犯。除此之外,仍有大量采取人权进路的案件处于审理阶段。

因为国际人权法以国家作为主要的约束对象,所以该类案件的原告多针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力。以企业为被告的诉讼进度则稍显缓慢,而且多以失败告终。但随着气候归因科学的进步、人权依据的创造性使用,剑指企业的诉讼开始取得突破。以目前最为引人关注的“地球之友诉荷兰皇家壳牌案”(Milieudefensie et al. v. Royal Dutch Shell plc.)为例,法院认定壳牌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违法,判决壳牌公司的减排额度至少应在2030年前达到2019年排放量的45%。本案引发了运用人权法要求非国家主体承担减排责任的诸多思考和尝试。
基于人权的气候诉讼何以可能?
虽然承认环境权是一种普遍人权的联大决议不能直接提供解决国家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不同公民之间争议的规则,但是却可以成为法院进行裁判时重要的论证依据。气候变化诉讼的一个典型特点在于法院常常通过综合应用各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佐证其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可以预期的是,各国法官将越来越多地从环境权出发进行司法论证。
采取人权进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让法官得以通过运用漏洞填补技术创造新规范,而不仅仅更新现有规范的解释。当前法律体系大部分的规范都先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而产生,所以既有法律无法应对气候治理之复杂需求的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常态。此时,可以主张法律中存在法律漏洞,需要法官创造出新的规范进行漏洞填补。司法为人民提供了对立法者和政府的决策提出异议的机会,使之有机会通过事实证据和法律论证的呈现说服法官,令法官在坚持法律基本价值的情况下让进步性的、有意义的变革出现在气候变化的法律与政策中。
当前法律体系大部分的规范都先于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而产生 […] 需要法官创造出新的规范进行漏洞填补。
人权进路的气候变化诉讼区别于一般气候案件的重要特点是,当事人和法官都诉诸法律原则进行论证。法律规范(legal norms)分成法律规则(rules)和法律原则(principles)两种。规则直接分配人们的权利、义务、责任,原则表达法律所追求价值的规范。原则既包括宪法性的基本原则,也包括成文或不成文的人权与基本权利承诺。尽管法律原则无法像法律规则那样直接运用于裁判,但是法官不仅可以通过把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则结合创造出新的规则,还可以通过仅使用原则判定现存的规则不足以实现对人权及基本权利的保护,进而要求立法机关或政府修改规则。每个时代的法官都要重新思考和定义生命权、私生活安宁权、平等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保护方式和程度。
诉诸人权规范的原则性规定能够要求私人企业为气候变化负责。据调查,世界上排放最多的100家企业对1988到2015年间71%的工业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但排放行为本身并不违法,而且法律无法溯及既往。所以,如何促使这些碳排巨头承担责任一直是一项法律难题。这一难题完全有可能通过诉诸人权来解决。为了保护个人或群体更基本、更重要的权利时,完全可以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自由。法官能够通过诉诸法律原则的论证说明,为什么将为填补漏洞而新创的法律规则适用于企业此前发生的生产经营行为会有利于保护人权。
人权进路面临何种局限?
但是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以人权为基础的气候诉讼获得胜诉的案件数量并不多。正是因为司法机关具有一定的功能局限性,以及此种气候诉讼对特定法文化背景具有强烈依赖性,使得基于人权的气候诉讼无法取得普遍成功。
在已有的气候诉讼案件中,实现胜诉最大的障碍仍然是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之间的严格界分。即便在人权进路的气候诉讼取得较大进展的欧洲地区,仍有许多法院并不愿意直接改变法律、甚至不愿意宣布规则中存在漏洞。至于美国,在法院不能处理公共政策问题的教条(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学说影响下,权力分立将成为更大的障碍。“奥克兰诉英荷石油公司案”(City of Oakland v. BP P.L.C)的判决就坚持,虽然化石能源使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得到确认,“但是,如何适当地平衡这些世界性的负面因素和能源本身的正面因素,以及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配这些优点和缺点的问题,需要我们的环境机构、我们的外交官、我们的行政部门,以及至少参议院的专业知识。”换言之,司法机关本身对处理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的犹豫仍然是通过诉讼推动气候政策的重要阻力。
除了权力分立制衡的掣肘之外,借助司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尴尬之处在于,司法机关无法动用官僚系统、警察,甚至军队去落实更积极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即使案件取得了胜诉的结果,法院判决政府应当施行更有力的减排行动,但政府却并没有表现出相匹配的政治意愿和实际行动,甚至存在倒施逆行的倾向。诉讼结果和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差距,气候变化诉讼的进展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本身的进展。
此外,凭借人权进路实现社会和政策转型,需要整个社会对人权重要性具有足够的共识。目前取得胜诉结果的气候诉讼都同其司法管辖区对人权话语具有较高的接受程度这一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使得气候变化诉讼的人权转型实例局限在较为狭窄的地理范围内,具体而言就是西欧和南美少数国家。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法文化都把权利理解为诉讼中的“王牌”。
中国为何投了弃权票?
上文提到,此次联大决议对环境权的承认与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之后半世纪的国际法和外交领域的发展密不可分。实际上,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对于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是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派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当时带队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唐克在发言中曾批评资本主义工业模式是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此后五十年间,中国成长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力量,对环境的态度也从一开始坚定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支持者,转变为国际合作领导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从宪法框架而言,中国的环境治理选择了一条国家主导的路线。
即便如此,中国仍选择对该项联合国决议投了弃权票。这恰恰和人权进路的特点息息相关。人权进路的优势在于为公民社会提供了从人权角度促使国家有所作为的渠道,并且通过设立法律原则使法官得以创造新的法律规则。然而,从宪法框架而言,中国的环境治理选择了一条国家主导的路线,体现在宪法把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国家任务加以规定,而没有选择承认环境权。不仅如此,中国的司法文化鼓励法官落实政策性的指引,却并不鼓励依据原则创造新的规则。更何况在国际人权领域内,环境权和其他人权的关系尚不明朗,在中国国内法中则尚未引入环境权的概念。在此语境下,中国选择投下弃权票并不令人惊讶。
具体在气候变化而言,中国采取了一种“发展主义路径”:气候治理主要是那些负责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国家机关的任务,气候政策以工业转型为目标,应对气候挑战不应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主义路径引导下生成了一种通过计划进行治理的模式——中国有大量关于气候的政策方案或计划,而与此同时,却几乎不存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在现有的《行政诉讼法》框架内,一般公民无法以权利受到侵害为由提出对于这些政策或者其执行的诉讼。这种治理模式当然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减排成效,并因此证明气候政策应对效果和是否采取人权进路没有逻辑关系。但是,该模式也存在着透明性、可归责性和公共参与不足的缺陷。即使气候诉讼的人权进路成为大势所趋,但由于中国的法律传统以及现实背景,该路径恐怕并不会在中国实现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