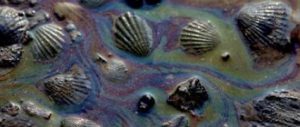大部分的时间里,艾米丽•莎克玻夫都在遥远的世界彼端冒着严寒为英国南极观测站进行大气涡旋和海洋涡流的观测。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却撸起袖子,横跨英国,直面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热议。
在“与环境变迁共存”组织的支持下,她与政府部门和投资机构合作,组织了一系列焦点小组座谈,从而了解人们对于媒体有关科学领域方面报道的看法。不仅如此,她还鼎力支持oldweather.org等项目的开展。该项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海面温度历史数据的分析。她在被借调到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的期间,还将视频上传到YouTube上 ,并且通过博客与那些“持怀疑观点的人”展开唇枪舌战。
“显然,科研人员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已经遭受了打击。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尽量把我们的研究过程向公众解释清楚,”她说道,“我一直在试图找到能够将我们的发现与大众进行沟通的方法。气候科学中有很多领域具有相当的难度,并且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我们真的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向公众解释我们所作的工作,让我们的工作被人们所理解,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莎克玻夫是跟那些拒绝接受主流科学的人进行斗争的新生代的先驱, 他积极地同各种批评进行较量,从转基因食品及核能到疫苗接种和动物实验。互联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双方利用网站、电子邮件、以及推特等方式在原本各自独立的个体间传递信息,并将他们联合起来。“持怀疑态度的人”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从压制信息自由法案对气候科学家的要求,到以诽谤罪指控那些对替代疗法持批判态度的人,使他们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其中,最具争议的当属全球气候变暖。而在人称“气候门”的东英格利亚大学邮件泄密事件中,所谓温度记录被篡改的问题更让公众对这一问题疑虑重重,并且开始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中所作出的预测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在这场辩论中, “怀疑论者”一词本身已经成为了斗争的一部分,那些质疑全球气候变暖的人则以怀疑论者自居。
“怀疑论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遗憾,这个词却被误用了,” 莎克玻夫表示,“这就造成了很多困扰。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赋予其正确的意义……这将是一个进步。”缪尔•罗素爵士在其针对气候门所作的报告中,对于人们认为研究人员缺乏严谨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质疑予以了驳斥,但他同时也呼吁科研人员应以一种更加坦诚的方式向其他相关群体公开自己的研究方法,使他们能够获得自己的研究结果及实验模型。他还呼吁科研人员通过博客对批评作出回应。就这几点而言,莎克玻夫堪为楷模。
在很多人看来,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二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约翰•贝丁顿爵士在《新科学家》网站上发表博文警告说:“当下,学界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向那些滥用科学证据的现象发起挑战。我们应该让大众能够获得并了解这些科学证据及其相关不确定性。在一个全球资讯发达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再自说自话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政策与交流主任鲍勃•沃德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人们如何接受科学,而是人们是否能够相信研究人员⋯⋯,科研人员并不擅长于对未知因素进行粉饰,从而让其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当你试图将研究代入决策领域时,不确定因素常常会被拿来当做不作为的借口。某些时候对不确定因素进行淡化并非是为了要蒙蔽大众,而是因为担心这些不确定因素会被某些人夸大,因为这些人能够从抵制可能采取的政策反应中获得利益。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对不确定因素进行解释。”
—
六月初,在位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格兰芝酒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似乎很满意于与十几位健康及发展部长在同一个平台上达成的共识。此次会议额外为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筹集捐款达43亿美元,用于为世界最贫困国家的儿童购买和接种疫苗。
然而会场外却聚集了一群抗议者,他们对疫苗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博士在1998年提出的自闭症与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MMR)有关的理论引起英美两国父母的担忧,导致儿童接种率下降。而抗议行为正是这一言论的反映。在会场内,当一名记者提出这一问题时,盖茨婉转而简短地表示大可不必为此担心。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不知道是否还对哪个医学问题进行过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
而二月份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当被问到自闭症与疫苗之间的联系时,盖茨的回答则更加直接,“这种说法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它夺去了数千名儿童的生命。由于很多母亲听信了这个谎言,没有给她们的孩子接种百日咳或麻疹疫苗,导致很多儿童死去。所以,那些参与并从事反疫苗运动的人,你们要知道,他们、他们是谋杀孩子的凶手。”
当下科研人员的所有争论中,对于疫苗安全性的疑虑是众多能够在短期内对人类生命造成极大威胁的问题之一。韦克菲尔德的论点提出后,英国MMR接种率便出现下降,并且在当前欧洲、美国、甚至非洲等地已经面临感染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导致它的激增,而感染的后果或者致命,或者影响生育能力。然而,在这么多人为了自己的孩子直面疫苗接种问题,并且后果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人们的措辞也会非常激烈。
“盖茨的言论应当被看作是一种仇恨言论,”曾帮助在微软纽约总部外组织抗议集会的玛丽•胡柏律师说道。作为一名曾在前苏联度过童年时代的人,她把“支持疫苗”的游说活动与集权主义相提并论。“集团的划分非常严格,市场被四家疫苗生产厂商所垄断,”她表示,“如果你有不同意见,你就会被贴上异类的标签。因此人们往往谨言慎行。”
而她的观点中有相当部分并非基于大量的科学实证,因为证据显示自闭症与疫苗无关。相反,她的观点是在少数持不同意见的研究以及美国赔偿判例的基础上得出的。美国对一些有可能受疫苗接种副作用影响的孩子家长进行了赔偿。她认为,“科学还远无定论。”在今年她与他人合作编撰的书中,她将其定性为“支持或反疫苗”阵营间的争论,称一些科学家是“疫苗伤害否定论者”。
这种观点对媒体的影响依然在持续着。牛津大学神经学教授科林·布莱克默尔爵士表示,“人们逐渐开始尊重科学,对科学方法及其局限性的理解也在逐渐加深。虽然互联网让反对之声变得更加清晰,但是我认为它并不会造成更大的影响。”他认为,正是在主流媒体的煽风点火下才引发了人们对于自闭症的担忧,而其试图在报道中对各方观点进行“平衡”的努力却不太成功。“如果将数据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话,他们就有能力做出决策。全国的媒体应当肩负起这个责任。”
而科研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则是找到与媒体打交道的最佳方式。费城儿童医院传染科主任保罗•奥菲特教授认为,“我们有责任就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向公众作出解释。但是,在你接受医师培训的过程中却从来没有人教给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媒体需要的是言简意赅。而政治中,你又不得不撒谎使诈,攻击他人,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但是,科学家们并不精于此道。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份温和的工作,在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房间里花了十年时间给小老鼠接种疫苗。”
他一直在不知疲倦地进行宣传,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并且还著书立说。在他的《死亡决策》一书中,对反疫苗运动进行了抨击。在他看来,丝毫没有乐观的余地。并且他还在书中引用了近期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否决“个人信仰”免疫接种豁免权的司法判例。而根据“个人信仰”免疫接种豁免之规定,父母可以不接受学校为其子女进行强制性免疫接种。但是,同时他也指出这一转变背后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并且与许多其它方面的争议相比,这个因素在免疫接种方面的影响更加显著。“钟摆之所以会回归,其原因就是传染病的爆发。2010年,加州爆发了1947年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百日咳疫情。”
英国卫生部免疫接种司司长大卫•索尔兹伯里同样对赢得这场有关疫苗的论战充满乐观。同时,他还强调说:“问题远比采取支持还是反对的立场要复杂。这是一个事关个人观点的问题。”他不仅以基础疫苗接种率的回升为例,还以民意调查结果作为佐证。在这些民意调查中,针对母亲是否会自动选择对她们的孩子进行疫苗接种,还是会难以作出抉择进行了调查。十年前,只有一半的母亲会毫无疑问地选择接种。而如今,有四分之三的母亲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接种。“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巧妙地处理问题。”他说道,“你不能用一个危险来对抗另一个危险。告诉人们麻疹同样会很危险,从而让人们在疫苗接种的后果间作出权衡。而家长也希望获得更多有关副作用的信息。”
当年韦克菲尔德的论点发表后,官方在应对MMR恐慌方面行动迟缓。索尔兹伯里认为,如今,有关方面在应对此类问题时行动要比过去更加迅速,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他以近期英国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接种为例。在其宣传过程中动用了包括聊天室在内的多种社交媒体。当一名女孩在接受注射不久后死亡的事情发生后,他强调说,卫生部门在事件调查清楚前并未发表任何看法,直到证明该名女孩是死于一种与疫苗无关的病症之后才公开发表声明。
然而,战斗还远未成功。两年前, 当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之时,人们对于疫苗数量不足的恐慌很快便被极低的接种率所引起的忧虑所取代。尽管抗病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但是接种率依然仅有40%左右。一些调查显示,人们对于副作用的疑虑和担忧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大卫•严斯是位于洛杉矶的加州大学的一位医学科研人员。去年10月,当他打开一封信的时候,一叠剃须刀片和一张死亡威胁信掉了出来。这是2006年开始的恐吓活动的最新一次行动,活动还曾试图用炸弹攻击他的一名同事。在2009年,行动升级为一次爆炸行动,炸毁了他自己的汽车。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退缩,还发起了一场关于动物实验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的活动。
他说:“他们把我的车炸毁不单单是为了吓唬我一个人,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害怕。当你坐在你的办公桌前,必须有非常强的动机才能让你离开你的计算机,而且如果你需要任何理由不去寻找动机,那么这种威胁已经帮你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可以很好地平衡暴力与我自己的主张之间的关系,这激励我采取我们本应该已经采取的行动。”
每个月都会有十几个示威者聚集在他家门前,高喊着下流的口号,打扰着他的邻居们;他们还高举着各种实验照片,他说这些照片跟他的工作和实验室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严斯也组织了一个反击小组,最近,有40名科学家团结一致地出现在他家门前,挡住了他家大门,举行了一场聚会。他还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各种会议,同投资机构、科学组织和动物保健机构建立起联系,并说服研究员们驳斥动物权益组织的请求。“绝大多数动物权益的活动分子并不想要进行一场辩论,他们也不会放弃。当他们能够阻止举行辩论时,他们就将成功。”
严斯成立的组织称作为科学支持实验,这是受到了英国一个类似的组织的启发,英国这个称作支持实验的组织最初是由一位名叫劳里•佩克劳福特的少年成立的,他对示威者反对在牛津大学建立一所新的动物实验室而感到困惑。两个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严斯的组织主要是由科学家所组成的,并且讨论他们自己的工作。
几年前这种回应看上去是无法想象的。在英国,在医药公司和学术界迟到的辩护引发了禁令和刑事诉讼之后,动物权益极端分子的活动已经逐渐平息下来。严斯说,在美国类似的方式受制于复杂的立法,其中包括宪法对言论自由的强大保护,诉讼也基本上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相信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辩护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说:“这背后并没有控制集团,但是在暴力不断升级的三年中,没有出现一次的暴力反抗,我认为这绝非偶然。”
严斯补充道:“写研究报告并不是作为一名科学家最终的工作,向我们的受训人员展示,科学家还是一名科研教师,一名同大众就科研进行交流的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我们逐渐地把它当成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这很实际,这同时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抛开这些华丽的辞藻,有证据表明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仍旧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甚至还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媒体以及互联网上的争论所产生的影响要比许多人相信的少很多。益普索-莫里系列调查最新一期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非常”或者“相当”相信为大学工作的科学家,尽管70%的人觉得有“太多的矛盾信息导致很难判断应该相信谁”,而只有43%的人相信他们了解科学知识。
伦敦大学学院地理学系主任马克•马斯林教授认为:“气候门并未对气候科学造成任何伤害。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英国的体系中气候变化政策已经占了多大比重,无论是对建筑物的规定、垃圾管理、还是能源供给系统等。在怀疑论者还在就气候变化进行争辩时,欧洲已经开始了一项数十亿欧元的碳交易计划,该计划将很快涵盖全球航空55%的排放。”
但是,他也同时呼吁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他强调“并非所有杰出的科学家都是杰出的外交家”,而且当有些科学家开始谈论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的时候,问题有可能就随之发生。马斯林教授认为科学应该有来自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实践者参与其中(例如来自社会科学和法律界),并鼓励“来自第一线”的人更大程度地参与进来。
他引述了最近召开的一次关于人口增长的会议,会上的许多发言人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他还引述了关于2010年的旱灾对亚马逊河的影响的最新研究, 这项研究凸显了巴西的科研人员的贡献。“这可比一个中年白人男科学家更有说服力。”
然而,苏塞克斯大学的安迪·斯特林却提出,人们应该对近来要求科研人员对于不同意见采取不容忍态度的呼声保持警惕。他强调,有不同意见在所难免。“呼吁民众对于怀疑论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反科学的。然而,有些时候,人们以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那些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领域。我们应该开始以一种成熟的态度展开辩论。”
然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关于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畅所欲言,很多科研人员都缺乏训练,而且也并不适合这项工作。此外,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似乎逐渐愿意反驳那些缺乏论据的批评,而且不仅仅是在他们的实验室里,还在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上。他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说服同行,同时也是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
安德鲁•杰克,金融时报医疗记者。
https://www.ft.com/home/uk
© 金融时报有限公司版权所有,2011年
首页图片来自绿色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