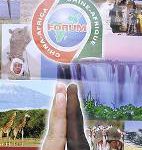根据官方数据显示,阿拉善荒漠化土地面积由1996年的92.71%上升到2004年的93.14%,增加了0.43个百分点。每增加0.1个百分点,意味着将增加200多平方公里的劣质土地。分布在阿拉善境内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三大沙漠日渐连成一片,在阿拉善左旗境内有3处“握手”、阿拉善右旗境内有4处“握手”区域。
阿拉善盟林业治沙局局长范·布和说:“人口的增加、牲畜的增加、农业的过度开发,是阿拉善生态恶化的根源所在。”
历史资料显示,阿拉善人口从解放初期的3万人膨胀到2005年末的21.2 万人,增加6.1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的增长。解放前宁夏军阀征兵,以及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饥荒,是大量外族移民迁入阿拉善的主要原因。
外来民族的冲击使得阿拉善原有的草原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口的增加促使了牲畜的增加。按照阿拉善目前的自然条件,全盟草场最佳承载量为70万羊单位。据2006年7月全盟统计数据表明,目前阿拉善有200万羊单位。
牧民们认为,官方数据并不足以采信,应该有少无多。譬如阿左旗贺兰队在1990年代养羊3万只,而政府的统计报告却只显示了1万只。
为了缓解草场压力并恢复生态,自1989年阿拉善左旗西滩和漫水滩开发建成之日起,阿拉善陆续展开规模庞大的移民搬迁工作,并在移民迁出区实施禁牧。1995年1月,时任盟委书记伏来旺提出“适度收缩、相对集中、转移发展”的“转移战略”,明确了从牧区移民向绿洲和城镇聚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思路。官方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末,全盟已搬迁转移牧业人口5676户、19082人,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继续搬迁牧业人口6520户、21754人。以全盟2005年末21.2万的人口计算,截至十一五末,阿拉善将总计实施生态移民40836人,约占其总人口的1/5,占牧民总量的4/5。
但是,解决环境问题却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阿拉善生态移民导致了大量牧民陷入贫困。
1999年,阿左旗政府作出了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实施退牧还林、移民搬迁的决定,共搬迁转移牧民1500户6000人,转移处理牲畜23万头,退耕3500亩。
牧民每人从政府处获得500元的安置费,贺兰山上被拆的羊圈一座补贴1000元,拆掉的砖房每平米补贴140元,土房100元。一二期移民政府4.95元/亩/年的补贴,补偿期限为5年。2001年开始的第三期搬迁,每亩土地牧民获得国家补偿11斤陈化粮。退牧搬迁之后,由牧民变为农民的移民最大的收入就是种植庄稼获得的农业收入,综合收入仅仅为禁牧之前的1/3。
记者来到苏木图嘎查(嘎查相当于乡)所在的移民区,牧民图木巴特正在院子里转悠,伺候着满地跑的几只小鸡。图木巴特说,自2005年退出草场后,家里卖掉了400多只羊,依靠政府的补贴过起了“闲民”生活。他全家7口人,每年可拿到十万多元的补偿款,补偿期为5年。
“5年之后呢?不让放牧了,也没有地种,政府也没有安排什么就业,我们只有闲着,养几只鸡鸭。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嘎查里还有好多。”图木巴特对往后日子表现出担忧。
阿拉善盟党校经济学副教授杨牡丹着重强调了移民的回流甚至沦为游民的问题。一份名为《内蒙古阿拉善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报告书》中显示,截至2004年,阿拉善约有3.4万牧民处于贫困线之下,0.47万牧民处于绝对贫困水平,许多地区已失去人畜生存条件,有2万多牧民沦为生态难民现已迁入他乡。
阿拉善盟副盟长龚家栋承认:“只有对移民的生产生活出路问题给予妥善解决,才是成功实施搬迁转移的重要保证,而仅以经济补偿进行安置是行不通的。”
阿拉善盟行署决定,将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的二三产业以接受移民就业。2006年初,阿拉善对“转移战略”进行了修正,由向“绿洲集中”转向“城镇集中”。与此同时,阿拉善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动愈发明显。
阿兰善盟环境监测站站长陶格日勒表示:“阿拉善的经济发展的确较快,年均达到30%的增速。GDP的增长主要来自工业。按照阿拉善盟十一五规划所言,在未来的5年中,还将有21754人沦为生态难民。杨牡丹认为,按照阿拉善的现有经济水平,能否容纳如此大的就业量,是一个问题。
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又致使污染加剧、生态恶化。在被视为阿拉善工业重镇的阿左旗吉兰太镇和乌斯太镇,因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已经成为国家环保局和土地部门重点监控的地区。从巴彦浩特到额济纳旗沿途的600多公里的路途中,公路沿途曾几乎荒芜一片,全为戈壁和沙漠。
该如何反思阿拉善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得失呢?
刘书润坚决反对草场围封转移,认为围封转移对草场不利、对人对牲畜不利,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
“牲畜适当的少对草场有利,没有牲畜的草场不行。”羊吃七百种草,牲畜吃草、踏草,既是促进又是抑制,并不都是坏事。没有这种作用,植物猛长,也是一种绿色消耗。而且,围封之后的草场没有牲畜粪便的浇灌,多年下来,只有一二种草能生存,将促使物种单一化。
刘书润指出,各种不合时宜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出台,根本原因在于小农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贬低,不经思考的移植汉族经验,并在阿拉善强行推行,只能说是政府的无知,是主流发展观的泛滥。刘书润甚至提出,游牧文化是阿拉善千百年来的自然选择,草原地区应该发展游牧以期社会重构。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秘书长邓仪表示,“多少年来政府保护生态不遗余力,但你可以发现一点,当人和自然来隔离开来,对自然进行恢复的时候就很有效果,拉一根铁丝网,理论上铁丝网围住了,牲畜对自然的压力就减少了。实际上,铁丝网是死的,人是活的,骆驼是大的,羊是小的,那么就是说,改变不了人,牧民的行为不发生变化,所有的治理也只是一个秀而已”。
该协会副会长宋军认为,中国政府在环保上鲜有作为的根本原因是,环保推进往往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也是项目执行者,却不是环保的利益主体。
宋军提出生态保护应该产业化,确定利益主体——政府充当出具优惠政策,生态保护由市场化主体实施运作,同时也让牧民参与进来,成为生态产业的受益者。
周季钢,曾供职于《经济》杂志和香港《凤凰周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和时政问题,擅长深度调查报道。他的有关包头核污染、中国大陆地下性产业等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