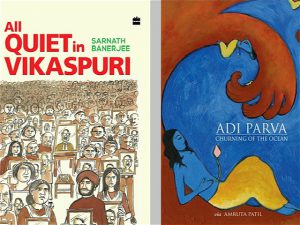这里是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最西部,大部分土地荒无人烟,显示在地图上的定居点少得可怜。曾经,从花拉子模绿洲流淌过来的阿姆河在这里注入世界第四大湖咸海。如今,阿姆河像地图上的一条裂纹,蜿蜒向北,远未到达曾经的终点就消失不见。
从阿姆河消失的地方一直到咸海的大片土地,在地图上是一块干净的空白。我决定去亲自看看,在真实的世界里,那片空白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首府努库斯,我雇了一辆三菱四驱车前往咸海。经过将近半天的跋涉,三菱车冲下高原,进入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细软的沙地上,散落着破碎的贝壳,植被全都干枯了,仿佛远古时代的遗骸。
咸海
司机停下车,指着远处,咸海终于出现在了丘陵的尽头处。尽管距离湖边尚有一段距离,但汽车已经无法开过去。我跳下车,徒步走向它。阳光明亮,但气温极低。天空是一片混沌的白。风吹在脸上,有一种咸咸的粘稠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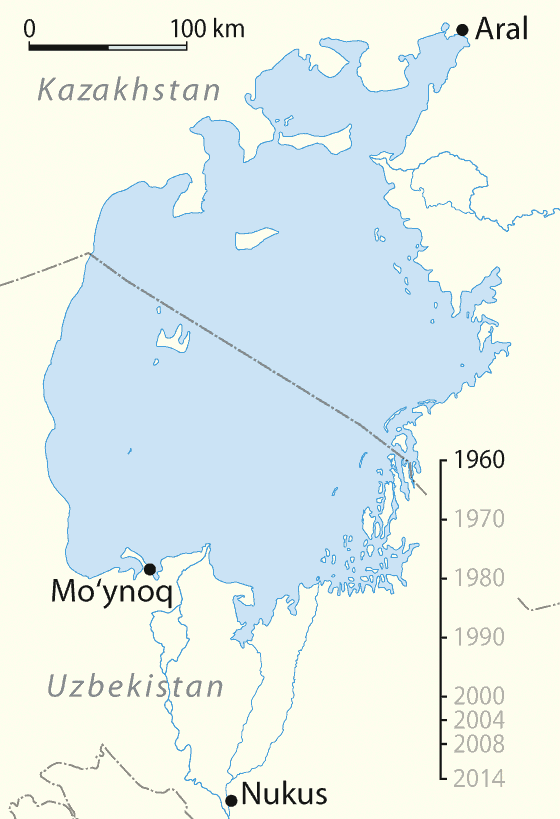 这里依然保留着湖底的样貌,呈现出月球表面般的荒凉形态,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荒凉感。日复一日,咸海缩减着自己的疆域,2012年时水量只剩下1960年的十分之一。
这里依然保留着湖底的样貌,呈现出月球表面般的荒凉形态,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荒凉感。日复一日,咸海缩减着自己的疆域,2012年时水量只剩下1960年的十分之一。
湖面是灰黑色的,平静得仿佛静止住了,就连浪也如同电影中的慢镜头,能够分辨出波动的褶皱和线条。我的目光无法看到更远的地方,因为远处的湖面被一团雾气弥漫的虚空吞噬,仿佛刻意想隐藏什么。
棉花
咸海的衰落与棉花密不可分。
19世纪,沙皇俄国开始把中亚地区变成棉花基地。棉花取代了当地农民栽种的传统食用作物,成为主要经济作物。1860年,中亚供应的棉花仅占俄罗斯棉花用量的7%。到了191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0%。
苏联时期延续了这样的做法。为了灌溉更多的棉花田,中亚的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人为改道。它们被沿途挥霍,灌溉越来越多的棉田。这导致两条大河还未及注入咸海,就在荒漠中蒸发殆尽。失去补给的咸海面积开始逐年缩减。按照现在的速度,很快就会从地球表面上消失。
长期种植单一作物,加之使用化肥,也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开始变得贫瘠。然而积重难返,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仍然保持着世界产棉大国的地位。2017年以前,所有中小学生都必须参加义务采棉劳动。每到采棉季节,运力不足的火车上会挤满流动的采棉女工。我在乌兹别克斯坦时,正是采棉时节。一位旅行者告诉我,他已经购票的火车被突然取消,因为要改成“采棉专列”。

正在棉田中采棉花的女工。乌兹别克斯坦是产棉大国。每到采棉季节,运力不足的火车上会挤满流动的采棉女工。摄影:刘子超
穆伊纳克
离开咸海,我前往一个叫作穆伊纳克(Muynak)的小镇。
仅仅几十年前,穆伊纳克还是咸海最大的港口,典型的鱼米之乡。1921年,苏联发生饥荒,列宁曾向穆伊纳克请求帮助。短短数日之内,21,000吨的咸海鱼罐头,便抵达了伏尔加河流域,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咸海水量减少后,盐分是过去的十几倍,鱼类已经无法生存。穆伊纳克的一万名渔民,因此失去了工作。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成为环境灾难最令人震撼的注脚。
如今,昔日的港口,距离湖水已经超过160公里。经过四个小时的颠簸,当三菱车驶入穆伊纳克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贫瘠而荒凉的小镇。到处是黄土和荒地,灰尘扑扑的石头房子,人们的脸上带着困居已久的木讷神色。
我来到曾经的码头,发现这里早已没有一滴水。干涸的海床一望无际,上面还搁浅着一排生锈的渔船。我顺着台阶,下到海床,走到渔船跟前。锈迹斑斑的船身上,依然能够分辨出当年的喷涂。船舱里,散落着酒瓶子和旧报纸,还有破碎的渔网。
海洋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渔船四周长出了一丛丛耐旱的荆棘。曾经,我的眼前遍布着渔船,如今大部分渔船都已被失业的渔民当作废铁变卖了。剩下的这十几条,成为沧海桑田的唯一证据。
我摸了一下船身。在红色铁锈之下,那些钢铁的肌理似乎仍在喘息。置身于这样的场景里,我不能不感到哑口无言。从费尔干纳山谷到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我一路上看到了那么多的棉田。它们养育着这个国度,却也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由于咸海的荒漠化,棉花种植耗费的大量农药残留沉积在土壤表层,风干成为有毒盐尘,可以顺风吹遍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甚至远至格鲁吉亚和俄罗斯。
救赎
早在苏联时代,政府就曾考虑从西伯利亚引水,救助咸海。但那是苏联时代的末期,庞大的帝国已经无力支撑如此宏大的工程。计划最终在1987年正式搁浅。
1994年,咸海流域中的五个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每年动用1%的政府预算,治理咸海。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主动削减棉花产量,承受由此带来的阵痛。那意味着让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治理实际上沦为空谈,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咸海的面积仍在加速缩减。1987年,咸海已经断流为南北两部分。2003年,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南咸海,又断流为东西两部分。
我站在港口旁的展示牌前,看着咸海近百年的变化图,回想着我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片巨大的空白。周围荒无人烟,只有被遗弃的房子。很多人已经举家搬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留在这里。
离开
我的司机告诉我,他原来就是穆伊纳克的渔民。十几年前,他咬牙变卖了渔船和家当,搬到努库斯,重新开始,后来才成为一名司机。他总结着自己的一生:他一辈子经历过两次巨变。第一次是苏联解体,那意味着国家和身份的转变;第二次则是咸海的消失,那意味着过去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就此终结。
那天中午,他带我去当年的邻居家吃饭。戴着头巾的女主人端出饭菜,然后悄悄退出了房间。她的丈夫也离开了这里,在别的城市打工挣钱。
午饭后,我们一起走到庭院。那是秋天最后的时光。一排排西伯利亚大雁,正在空中变幻着队列,准备飞往南方过冬。我们静静地看着大雁,想象着它们一路的飞行。然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开始对着天空拍照。
因为,在这里,如此生机勃勃的场景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