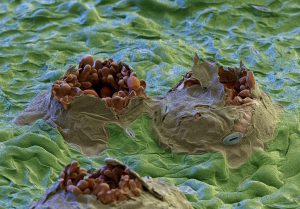对“自然”的理解,也包括理解我们与它的关系。在2003年,我在为《烈日下的老虎》这本书做田野调查时,确信了这一点。这本书描述了亚洲各地的老虎保护工作,在前往中国东北调查那里野生虎真实种群数量的途中,我在上海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会上,人们提到我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后代,两个女孩会后很兴奋地来找我,因为达尔文在是中国如此重要,用她俩的话说,他代表着“人类的进步”。
对我而言,达尔文首先代表的是我们与其它物种的连通性,因为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在以自然为代价来实现人类“发展”的中国,目前的文化气候凸显出人与动物的割离。除了动物学家,我在中国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把对动物的利用、享受、主宰和消费视为一项人类权利。
在上述对达尔文态度的差别背后,是全然不同的文化遗产。中国人之所以持那样的观点,部分原因是历史上自然确给他们带来了可怕的威胁。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同时也是“中国的悲哀”,大洪灾吞噬了无数生命,堤坝修建者在中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如今,中国的河流,首先是长江,正在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悲哀:干涸、污染、动物群落消亡、因人类的作为而威胁到环境。由于工业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黄河的三分之一已经不能再用于农业或工业,新建的大坝业已毁灭了人类福祉赖以维系的自然。
你可以把对一部分自然(比如其它物种)的理解比做学习另一种语言。你要掌握关于动物的生物学、行为特征和生态学,就像你要学习语言中的语法、句法和词汇。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脱离现实地学习另一门语言。你必须在相互联系中来学习,通过弄清外语词汇与母语词汇的对应关系、通过翻译学会这些词。
要了解其它的动物种类,你必然按照那些你的特有文化给定的方式来认识它。要了解一种动物,你不仅要弄清它生活的地方(它的猎物、天敌、栖息地、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还要弄清那些试图了解它们的人——你是谁、你以及你的了解方式来自何处、你的认识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换句话说,要弄清动物与人类文化的关系。
人类永远都是象征性的追求者。我们把外在的事物赋予内在的意义,在这个物种大量消亡的时代,一种动物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有助于确定这一物种是否仍然存在。在《烈日下的老虎》一书中,我力图把老虎放在每个国家的艺术、宗教和历史的象征性网络中来探讨。例如,老虎在不丹的生存几率比在中国更大,因为前者将其视为佛教的保护神,后者则其视为一种令人着迷的凶猛象征(中国人认为食用老虎身上的某些部分能强身健体),这就是物种在不同文化中象征意义的区别。
瓦尔米克·塔帕
在《虎崇拜》一书中,塔帕探讨了老虎在亚洲各地的崇拜及其表现。他沮丧地指出,随着老虎崇拜在各国的逐渐消亡,这种动物自身也面临着偷猎者和栖息地丧失带来的威胁。
 在其近作《外来异种:印度的狮子和猎豹》一书中,他探讨了狮子从古代的中东、腓尼基、巴比伦、亚述和巴勒斯坦到现代印度的象征主义。塔帕穿越错综复杂的艺术史,记述了莫卧儿王朝从非洲进口野生动物,用于皇家苑囿和猎场的历史,并且尖锐地指出无论狮子还是猎豹都不是印度次大陆土生土长的。他还展现了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象征来强化其在他人眼中的地位,即:用“它们”在“他们”面前来象征“他们”。
在其近作《外来异种:印度的狮子和猎豹》一书中,他探讨了狮子从古代的中东、腓尼基、巴比伦、亚述和巴勒斯坦到现代印度的象征主义。塔帕穿越错综复杂的艺术史,记述了莫卧儿王朝从非洲进口野生动物,用于皇家苑囿和猎场的历史,并且尖锐地指出无论狮子还是猎豹都不是印度次大陆土生土长的。他还展现了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象征来强化其在他人眼中的地位,即:用“它们”在“他们”面前来象征“他们”。
《最后的熊猫 》
乔治·夏勒
1988年,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和妻子一起到中国的偏远地区研究大熊猫,这些熊猫据说因为箭竹开花枯萎而数量减少。但夏勒发现,真正的原因是熊猫被捉住并卖到动物园,而圈养的熊猫常常会死掉。从那以后,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中国也日益认识到必须让野生动物生活在其栖息地。

在这本书里,一位热爱自己工作的伟大科学家对生活在其栖息地上的野生动物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记录。在中国的时候,他向狩猎者发放卡片,上面写道:“所有物种都会因惩罚而颤抖。对所有物种来说,生命都是宝贵的。以己度物,我们不应杀戮或引起杀戮。”
但这本书也是关于动物在人类文化中命运的寓言。在“熊猫租借”计划下,中国将这些迟缓、脆弱、濒危的家伙出租到全球各地换取高额租金。这本书的跳跃很大,从对大熊猫在潮湿竹林中的描述,一下转到了它们与人类的联系以及它们成为国际政治中“典当品”的不讨喜角色等尖锐问题上,
约翰·珀林
 从人类文化开始之日起,木材就是人类的主要燃料和建筑材料,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依然如此。珀林描述了从古美索不达米亚以来,文化因为其对森林的利用而繁荣兴起,也因为森林的耗尽而衰落。古代的吉尔伽美什与“森林恶魔”斗争,砍光了不可代替的雪松林,最终将这片土地变成荒漠。从古巴比伦由于木材日益稀缺而强行征收的“门税”,到森林在英格兰与其美洲殖民地的斗争中发挥的中枢作用,这本书可谓一节令人荡气回肠的实物教学课,描绘了人类文化对自然既依赖又毁灭的方式。
从人类文化开始之日起,木材就是人类的主要燃料和建筑材料,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依然如此。珀林描述了从古美索不达米亚以来,文化因为其对森林的利用而繁荣兴起,也因为森林的耗尽而衰落。古代的吉尔伽美什与“森林恶魔”斗争,砍光了不可代替的雪松林,最终将这片土地变成荒漠。从古巴比伦由于木材日益稀缺而强行征收的“门税”,到森林在英格兰与其美洲殖民地的斗争中发挥的中枢作用,这本书可谓一节令人荡气回肠的实物教学课,描绘了人类文化对自然既依赖又毁灭的方式。
《流动的天空》
蒂姆·狄
 这本书里充满了一个诗人兼自然主义者所需的一切精细观察。这是一本关于鸟类对人类意义的书;是一本关于诗歌和成长的书;是一本关于对观鸟的需求和爱和对诗歌一样多的书。它拥有自己的美丽语言,一只红尾鸲被比作一片“美味的锈迹”,说明作者无论对于自然世界还是语言的观察习惯,可以将自然完完全全、淋漓尽致地转译到文化之中。
这本书里充满了一个诗人兼自然主义者所需的一切精细观察。这是一本关于鸟类对人类意义的书;是一本关于诗歌和成长的书;是一本关于对观鸟的需求和爱和对诗歌一样多的书。它拥有自己的美丽语言,一只红尾鸲被比作一片“美味的锈迹”,说明作者无论对于自然世界还是语言的观察习惯,可以将自然完完全全、淋漓尽致地转译到文化之中。
翻译:奇芳
 《
《